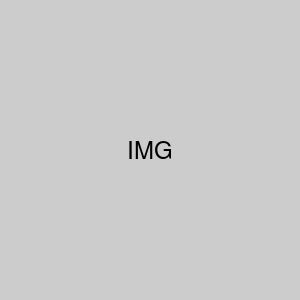在中國的冷戰關鍵期,閻明復被推入政局漩渦。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蘇聯結盟、以及後來轉而交惡的時期,閻明復都是毛澤東的俄語翻譯。1989年,當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彌合裂痕,他再次成為中方領導人的陪同。
但閻明復一生中經歷的最激烈、可能也是令他最痛苦的政治事件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民主抗議,此事給戈爾巴喬夫的訪問蒙上了陰影。閻明復成為談判代表,與抗議者以及試圖阻止血腥鎮壓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話。
“閻明復先生一生都是追隨共產黨的體制內人士,但是在1989年那個關鍵時刻,他的人性戰勝了黨性,”1989年抗議活動的學生領袖、現居美國的王丹在悼詞中寫道。“這樣的人在中共內部很罕見。” ,
储百亮阎明复曾担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天安门抗议期间,他作为谈判代表与学生对话,试图化解对峙僵局,后来遭降职。学生领袖王丹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人性战胜了党性”。 |
----
不知歸處:茨威格的流亡人生
作者: [美]普羅尼克(George Prochnik)
出版社:三聯
出版時間:2023年04月
人民幣 ¥79
ISBN:9787108075215
內容簡介
2014年美國國家猶太圖書獎傳記類獲獎作品
2014年前言評論INDIEFAB年度圖書獎傳記類提名
作者簡介
喬治•普羅尼克(George Prochnik)
小說家,人物傳記作家,自由編輯,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教授英美文學。著有《追求寧靜》《普特南隱身之所》等。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從奧德賽到俄狄浦斯……………………………………… 1
第二章 乞丐與橋…………………………………………………… 24
第三章 愛書之人…………………………………………………… 51
第四章 出走的本源………………………………………………… 82
第五章 重聚……………………………………………………… 105
第六章 到咖啡館去!…………………………………………… 126
第七章 全球輪盤………………………………………………… 154
第八章 教育之債………………………………………………… 180
第九章 告別美國………………………………………………… 205
第十章 戰時花園………………………………………………… 219
第十一章 田園牧歌式的流亡…………………………………… 242
第十二章 避難所………………………………………………… 263
後 記……………………………………………………………… 294
致 謝……………………………………………………………… 309
注 解……………………………………………………………… 312
《不知歸處》評論 ………………………………………………… 342
線上試讀
前言
1941 年 11 月某天臨近中午時,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一張窄窄的鐵床上醒來,另一張鐵床上睡著他的妻子洛特(Lotte)。他從玻璃杯裡取出假牙,穿上皺巴巴的長褲和襯衫。一群馬從他寓所旁的石路上橐橐地走過,棲在樹冠上的鳥兒們尖聲叫著,一些蟲子悄悄爬過他的皮膚。這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學名人、人道主義者,同西格蒙德•佛洛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湯瑪斯•曼、赫爾曼•黑塞及阿圖羅•托斯卡尼尼是好朋友,來自維也納,習慣用紫墨水寫作,總是穿燕尾服出遊,即將迎來他的 60歲生日。
點著今天的第一支雪茄,他從散發著黴味的小木屋走出,沿著繡球花雜生的陡峭臺階而下,穿過馬路,走進優雅咖啡館(Café Elegante)。在那裡,他坐在一群黑皮膚的騾夫中間,花了半便士享用美味的咖啡,和同他合得來的老闆練習了葡萄牙語。這並非易事,因為他的西班牙語總是跳出來礙事。之後,他又重新登上那些臺階,在兼作客廳的遊廊裡坐著工作好幾個小時,時不時抬起頭,越過棕櫚樹翠綠色的扇形葉子望向壯美的瑪律山脈。比他小 27 歲,曾做過他秘書的洛特,就在不遠處校正他那部關於國際象棋的短篇小說,女僕正在室內努力對付冒煙的爐子。在用過雞肉、米飯和豆子構成的“原始”的午餐後,茨威格和洛特按照一本國際象棋大師的棋譜下了一盤國際象棋。棋局結束後,他們進行了一次漫長的散步。此時他們居住在里約熱內盧山中的一個名叫彼得羅波利斯(Petrópolis)的小鎮。他們沿著小鎮主街走,又轉到一條古老的小徑,來到一處開滿野花和有些許流水的風景如畫的叢林。而後再回到小木屋,繼續工作,寫信回信。閱讀從地下室發現的一本蒙塵的蒙田著作並認真做了筆記(他寫道:“在我們的和平、獨立、天賦的權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識形態的狂熱犧牲掉的那樣一些歷史時代裡,對一個不願為這樣的時代而喪失自己的人性的人來說,一切一切的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唯一的問題,那就是:我怎樣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繼而入睡。如此這般,日復一日,月複一月。
但在今天,這種令人絕難相信的處境擊敗了他。在寫給洛特家人的一封信裡,他表達了自己的驚異:“我不敢相信,在 60 歲這年,我會身處巴西一個小山村,只有一個光腳的黑人女僕,同往日生活中的那些書籍、音樂會、朋友和交談相隔萬里。”他留在奧地利的所有財產,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家族紡織行業裡的股份,在1934 年第一次流亡時他設法帶到英國的部分家產,他都當數丟失了。他窮盡一生,費盡心血收集的大批名人手稿和音樂曲譜散落在
世界各地。在寫給倫敦的嫂子的信中,他再次寫道:“我最迫切的願望是,你能讓所有那些衣服、亞麻布、大衣等我們留在那裡的所有東西物盡其用……這就算幫了我大忙。對那些今生無緣再見的東西,我也會少些遺憾。”
但這裡也有一些特別的事情,儘管迄今為止他們遠離了構成往昔生活的所有要素,茨威格聲稱,“在這裡我們感到非常快樂”。這裡風景異常優美,當地人民淳樸可愛,物價很低,而且生活多姿多彩。他和洛特在積攢必要的力量去面對艱難的世道——“唉,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力量。”他寫道。只要想到被無法言說的苦難吞沒的家園,他們的快樂就會被破壞。關於納粹佔領區日常生活的新聞,甚至比軍事情況的報導更讓人沮喪。茨威格擔心他在巴西陶醉於
和平與繁榮時,成千上萬的人正在挨餓。巴西對歐洲爆發的自我毀滅的戰爭免疫,這在其當權者中引發了一種新的國家主義,他們開始幻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左右戰局。幸好善良的巴西人民一直未變。“我們希望能給你寄一些當地非常便宜的巧克力或咖啡和糖,”他寫道,“但一直找不到任何機會。”隱居在鬱鬱蔥蔥的彼得羅波利斯的茨威格寫道,歐洲如今的困境是遠超巴西當地人想像的,就像中國之前的掙扎對他這樣的歐洲人來說無法理解一樣,既認為不可能,又一直放不下。為什麼這個享譽世界文壇的作家,這個為自己的文學成就了驕傲,更為能夠團結起歐洲文學界和藝術界而自豪的人會蟄居在貢薩爾維斯•迪亞斯街 34 號,過著他自稱為修士般的生活?但也正是這種距離,這種茨威格向他的出版商描述為“完全與世隔絕”的巴西避難時光,使他保持了自由。在這段時間裡,他完成了自傳《昨日的世界》
,並“從頭到尾修訂”了之前的創作。彼得羅波利斯的鄉村生活“似乎將奧地利翻譯為一種熱帶的語言”,他對一位元流亡同胞如是說。對茨威格而言,維也納在黑暗中愈行愈遠,但這座城市作為一個藝術烏托邦的虛構角色卻愈來愈清晰。在這個意義上,他和他的老朋友約瑟夫•羅斯(Joseph Roth)有些相似,有人曾這樣描述羅斯:“隨著奧地利版圖的不斷縮小,他的奧地利愛國主義愈加強烈,這一情緒在其家鄉淪陷後達到頂峰。”
驢隊馱著香蕉從下麵的道路經過,女僕在隔壁廚房裡輕聲唱歌,茨威格忍不住開始回顧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時光。他最珍視的是 1888 年老城堡劇院(Burgtheater)被拆毀之前,維也納人最後一次齊聚這座宏偉建築時的場景,因為這證明了他生活的社會環境對審美的熱忱。最後一場演出的帷幕剛剛落下,茨威格寫道,悲傷的觀眾紛紛湧上舞臺,只為能撿到一塊舞臺地板的碎片——“他們喜愛的藝術家們曾在這塊地板上演出過”。多年之後,在維也納環城大道附近許多資產階級裝飾華麗的家裡,那些碎片“被保存在精緻的小盒子裡,就像神聖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裡一樣”。茨威格總結道,這完全是維也納各階層參與的“對戲劇藝術的狂熱”。此外,這種強烈的癡迷——不只欣賞,還有吹捧——也促使藝術家在創造性方面達到新的高度,他宣稱,“當藝術總是在其成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師的地方達到它的頂峰”。他從紙張上抬起頭,滿目皆是墨綠和金黃色的棕櫚,是翠綠中掩映的山巒,是廣袤的空蕩蕩的天空。他生命中的那些人都去了哪裡,他驚訝地想。茨威格是個精於世故的人,他原以為他已聽過世間所有的聲音,卻從未聽到過如他的新家這般的寂靜。
世上有一種天才,他們的獨樹一幟吸引著人們去探究在這些天賦異稟或邪惡之後的秘密。同時,世上還有另一種備受矚目的人,他們雖然不是天才,卻像是強效的透視鏡,折射出歷史上的重大時刻。
斯蒂芬•茨威格,這個富有的奧地利公民,焦慮的流亡猶太人,了不起的多產作家,不知疲倦的全歐人道主義宣導者,社交達人,無懈可擊的東道主,高貴的和平主義者,平民主義的捍衛者,神經質的感覺論者,愛狗厭貓人士,書籍收藏家,總是穿鱷魚皮皮鞋的人、衣著華麗、神情抑鬱的咖啡狂熱分子,世上孤獨的心靈同情者,偶爾沉迷女色、時不時與男子眉目傳情之人,疑似暴露狂,被定罪的謊言家,權貴的阿諛者,弱勢群體的捍衛者,隨著衰老
開始變得怯懦,在死亡面前又成了一個堅定的禁欲主義者——斯蒂芬•茨威格身上兼具了人類社會中誘人和墮落的魅力。
時至今日,茨威格的作品在歐洲依舊擁有生命力。他的中篇小說在法國經常再版,而且總是登上暢銷書榜單,他的作品遍及商店的櫥窗和機場的傳送帶。茨威格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同樣受歡迎,在德國和奧地利也有大批的崇拜者。但是在英語國家裡,尤其是美國,茨威格的作品在幾年前卻幾乎絕跡。在我長大並開始接觸文學的歲月中,我從沒見過任何一部茨威格的著作,而我的朋友之中幾乎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當我瞭解到 20 世紀 40 年代北美的學者是如何狂熱地對茨威格進行研讀之後,他的作品如今這種大面積的絕跡令我非常困惑。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茨威格如此迅速地淡出了公眾的視野呢?
他幾乎所有的故事都在揭示戰前歐洲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生涯讓人瞭解到,在這種文化被翻譯成新世界的風格時,是具有煽動性的。茨威格的人生闡釋了在危機四伏之時藝術家的責任感這一永恆不變的命題:忠於靈感還是忠於人文關懷,政治在藝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藝術所發揮的教育作用。他的生平引出了人類的歸屬這一問題——是我們對家庭和民族的責任,還是最終理想的世界主義。他在寫作中描繪過的形形色色的生命,他在薩爾斯堡家
中“露臺避難所”斑駁的樹蔭下,曾與許多歐洲的人道主義者和藝術家交談,這一切都使茨威格成為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裡不可或缺的催化劑和重要的橋樑。在自傳《昨日的世界》的題辭中,他寫道:“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這句引自莎士比亞的話,在茨威格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著不同的詮釋。
茨威格意識到,他自己從榮耀到困窘的陷落只是歐洲所處的巨大困境的一斑。他在《昨日的世界》的序言中曾這樣宣稱:“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的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但即使是這種共通的悲劇也無法緩解此般墮落對他造成的衝擊。自他被從歐洲文藝界的“奧林匹斯”驅逐至後來淒慘流浪的幾年中,他從未停止過詫異和震驚。“由於我脫離了所有的根系,甚至脫離了滋養這些根系的土地——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真的非常少見。”他這種時不時源自“莊嚴不復”的想像的呼號,總帶有些殉難者的意味。
1941 年夏,在由美國奔赴巴西的前幾天,茨威格寫下了這些序言。當時他住在紐約州的奧西寧(Ossining)是在這裡完成了自傳的初稿。如果說他在彼得羅波利斯的家是偏僻、荒涼的,那麼這所位於哈德遜河鎮,距新新監獄(Sing Sing)一英里(約合 1.6 千米)之遙的住宅則是窘迫和孤獨的。洛特在給遠在英國的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奧西寧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也沒有什麼美麗的風光可以去欣賞。”事實上,當地唯一據說著名的地方就是新新監獄,洛特寫道,“但每個人都試圖忘掉這點”。茨威格的朋友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歐洲筆會的主席,曾對這個他稱之為“陰森的郊區”的住宅提出過質疑,他擔心這樣的住宅可能會令茨威格的精神更加消沉。
在七月的一個下午,茨威格第一任妻子與前夫的女兒蘇斯•溫特尼茨(Suse Winternitz)在拉馬波路(Ramopo Road)7 號住宅的草坪上為他拍了一系列照片。他坐在一張籐椅上,同平時一樣,衣著整潔,一絲不苟:柔軟的淺色長褲,白色的襯衫和波爾卡圓點的領結。雖然已經 59 歲,但他修剪整潔的鬍鬚和從額頭向後梳的頭髮依舊漆黑,雙眼深邃。只有眼角的魚尾紋和嚴重的眼袋顯露出他的實際年齡。他身子前傾,翹著右腿,可能正傾向對話者。在那天拍攝的照片之中,有一張他姿態緊繃,表明他剛剛聽到什麼感興趣的事情。另一張裡面,氣氛放鬆下來,但他看起來卻仿佛是世界上最悲傷的人。在這兩張照片中,他的目光都透露出一種凝重。人們經常評論茨威格像鳥一般優雅的社交禮儀,但在這些照片之中,鳥兒卻一頭撞到它誤以為是天空的玻璃上。
在自傳中,他察覺到“在我的昨日和今天之間,在我的青雲直上和式微衰落之間是如此不同,以致我有時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過的生活並不僅僅是一種,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幾種”。他被迫“像罪犯一樣”逃離了“國際化大都市”維也納,他在那裡他長大成人,備受青睞,汲取文化養料並且成為咖啡館聚會的貴賓。茨威格在流亡美國期間經歷的戲劇般的絕境,對每個見過他的人來說,都是明顯能夠察覺到的。1941 年 7 月陽光燦爛的一天,克勞斯•曼(Klaus Mann)在紐約第五大道遇見了他。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發現這個曾被他稱為“不知疲倦發揮天賦的人”看起來與往常迥異——不修邊幅且神情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緒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沒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時候,茨威格才“像一個夢遊者聽到自己的名字”一樣驚醒過來,突然變回人們熟悉的那個優雅的世界主義者。儘管如此,曼仍然無法忘卻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時他那荒涼的眼神。幾周後,流亡的劇作家卡爾•楚克邁耶(Carl Zuckmayer)和茨威格一起用了晚餐。茨威格問他,繼續像個影子一樣活著,到底還有什麼意義。“我們都只是幽靈——或記憶而已”,茨威格總結道。
最重要的是,茨威格明白流亡從不會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過程。“你才剛開始流亡生活,”他在 1940 年曾對安德列•莫洛亞(André Maurois)這樣說,“你會看到世界是如何一點點地抗拒這種流亡的。”那時,茨威格已經在歐洲來回遊歷了很長時間。
他向一個朋友概括自己當時的處境:“前任作家,現為簽證專家。”他們從 1940 年 3 月到 1941 年 8 月底離開奧西寧為止,帶有日期、印章、簽字和手寫號碼的領事圖章,還有入境資訊極其詳細的登記和有效期,都被記錄在茨威格的英國護照上。滿滿 19 頁既稠密又神秘的記錄,仿佛是《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裡刻著玄妙咒語的護身符。
怎樣才算得上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概率是由其內心的剛毅程度、思想的開放程度以及外界的支持組成的方程式決定的嗎?為什麼湯瑪斯•曼、卡爾•楚克梅爾以及茨威格的指揮家朋友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可以在美國大放異彩,而茨威格、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和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爾(Ernst Toller)卻在新大陸的各種遭遇面前選擇了退縮?戈培爾(Goebbels)曾經嘲笑這些流亡的作家,把他們稱為“行屍走肉”。
這輕蔑的稱呼一針見血地點明瞭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懼,茨威格就曾被這種恐懼折磨:這種將驅逐、分離視為永別的恐懼。這對歐洲社會來說全然的恐懼,在新世界的海岸邊又再次出現。“二戰”期間,移居國外的藝術家和學者數量驚人,有歷史學家把此種情形同拜占庭帝國隕落後希臘學者的逃離相提並論。茨威格的美國歷程,通過這個新世界各地的酒店——一連串的房間,從一個不名之地到另一個不名之地間無法實現的航班中成百上千的車站——折射出 20 世紀 40 年代歐洲支離破碎的思想的停滯。所有的大堂和咖啡館裡都擠滿了流亡者,他們穿著寬鬆的褲子和笨重的大衣,彼此用母語低聲抱怨。在從那個地獄般的政府機構弄到證件、工作及工作證明前,他們就居留在偏離市中心的社區裡的長椅上,在那裡,早期流亡者的遺物,甚至一家商店,一個名字,一棟建築物的殘骸都會喚起他們對家的懷念。
布魯諾•瓦爾特將快樂流亡的秘訣歸為銘記“這裡”和“那裡”的區別。作為受挫的流亡者的典型,茨威格的流亡歷程堪稱毀滅性的——或可稱之為“羅得妻子綜合征”。他過度解讀了故鄉和當下環境的差異,並且總是忍不住回望過去。他在拉馬波路 7 號撰寫的回憶錄寫道,如今他們“像半個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淵中摸索”,“不斷仰望”那業已失去的大陸上的“曾經照耀過我童年的昔日星辰”。
在我們這個文化價值永遠錯位、顛倒的時代,茨威格親歷了世界在他面前一點點變陌生的過程——他喪失了故土、母語、文化的參照、朋友、書籍、使命感和希望。他的經歷不僅令人感傷,還神秘晦澀。這不禁使人想起湯瑪斯•曼的兄弟亨利希•曼(Heinrich)的一句話:“被征服者是最先體會到歷史蘊藏了什麼的人。”
(節選自《不知歸處:茨威格的流亡人生》,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4月出版)
陳耀昌向施江南先生、夫人施陳焦桐女士和他們的家人致敬
時代治癒所
紀念228的新模式,以紀念、堅毅,來代表替悲情。
四方醫院、歷史遺跡、罹難者事畧、家族紀念文、歷史文件、時代歌聲。
1935 年施江南醫師在臺北市天水路開設「四方醫院」,直到 1947 年 3 月 11 日之前,這裡是施江南醫師發揮所學行醫救人、實現理想投入社會公益的所在。而最終,施江南醫師也在這裡留下最後的身影。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團隊經過三年調查研究,有感於施江南醫師與施陳焦桐女士的故事對於當代社會的重大意義,在獲得四方醫院舊址現任屋主支持後開啟了策展規劃工作,以「時代治癒所」為題,融合李火增攝影家作品與施家捐贈文物,在天水路 25 號多年閒置的空間進行展覽,透過多元展示手法探究四方醫院的過往,並敘述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四方醫院施江南主治醫師生平事蹟,及遺孀施陳焦桐女士遭逢巨變後獨力支撐家庭的故事。
時代治癒所_四方醫院特展
展覽地點 :台北市大同區天水路 25號
開展時間 : 2023年6月1日-10月28日每週四 、五、六 10:00-18:00(展期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 )
策劃執行 :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協同策展人 :張維修
展場資訊及團體導覽聯繫 : tw.ihrm@gmail.com
聯絡電話 : 張仁豪 0963-535316 林哲彣 0975-500200
 已故裕仁天皇(資料照片)口述的《昭和天皇獨白錄》原稿二卷,以27.5萬美元拍出。美聯社
已故裕仁天皇(資料照片)口述的《昭和天皇獨白錄》原稿二卷,以27.5萬美元拍出。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