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同事們認為他的觀點比他的數據更危險時,E. O. 威爾遜一夜之間就成了美國科學界最令人憎恨的人之一。
愛德華·O·威爾遜預料到有人會反對他的觀點,但他沒想到自己會被當成罪犯對待。
到了1970年代中期,威爾森已經是世界頂尖的生物學家之一,這位哈佛大學的教授曾以近乎痴迷的精確度繪製出螞蟻社會的地圖。螞蟻只是他的掩護。他真正研究的是行為本身:模式、合作、等級、利他主義,以及一個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演化塑造了社會行為,而不僅僅是身體。
1975年,他出版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
其中一章引爆了一切。
威爾森認為,行為有著演化的根源,即使在人類身上也是如此。不是命運,也不是道德,而是影響、機率以及與文化的互動。他的措辭謹慎,但人們的反應卻截然不同。激進的學者指責他復興了優生學,抗議者衝擊了他的演講。請願書要求哈佛大學讓他保持沉默。他的名字成了燙手山芋。
然後,1978年來了。在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上,威爾森正準備發言,一位同行學者走上前,將一壺冰水潑在他頭上。有人高喊,他的著作為種族主義和壓迫辯護。相機快門聲此起彼落。訊息很明確。辯論結束了。懲罰開始了。
威爾遜全身濕透,沉默不語。
他沒有撤回那本書。他沒有道歉。他沒有為了安全而放棄清晰的論述。相反,他做了批評者無法阻止的一件事:繼續發表著作。他修改論點。補充數據。澄清局限性。他堅持認為,解釋行為並不能為不公義開脫,無知也從來不能保護任何人免受濫用權力之害。
代價是實實在在的。合作關係終止了。朋友們疏遠了他。要獲得研究經費變得越來越難。多年來,「威爾遜」成了爭議的代名詞。但生物學一直在發展,而且一直朝著他的方向發展。
他的思想悄悄被整個領域吸收。
行為生態學蓬勃發展。演化心理學興起。保育生物學採納了他的理論架構。那些曾經對他大加撻伐的學者們,開始教導他論點的溫和版本。他們沒有道歉。進步很少伴隨著道歉。
威爾遜轉而發出更宏大的警告。他開始記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計算物種滅絕率,並論證人類正在瓦解自身賴以生存的系統。他提議保護地球的一半,以維護生命本身。批評者再次稱他極端。但數學再次無視這些。
E.O.威爾遜並非因為粗心大意而引發爭議,而是因為他走在了時代的前沿。他最終明白了所有真理捍衛者都會明白的道理:機構會原諒錯誤,但不會原諒過早的決策。
他並非因為其思想令人憎惡而遭到攻擊,而是因為他的思想難以被控制。
E. O. Wilson became one of the most hated men in American science overnight when colleagues decided his ideas were more dangerous than his data.
Edward O. Wilson expected disagreement. He did not expect to be treated like a criminal.
By the mid-1970s, Wilson was already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biologists, a Harvard professor who had mapped ant societies with obsessive precision. Ants were his cover. What he was really studying was behavior itself. Patterns. Cooperation. Hierarchy. Altruism. And the uncomfortable possibility that evolution shaped social behavior, not just bodies.
In 1975, he published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One chapter detonated everything.
Wilson argued that behavior had evolutionary roots, even in humans. Not destiny. Not morality. Influence. Probability. Interaction with culture. His language was cautious. The reaction was not. Activist scholars accused him of reviving eugenics. Protesters stormed his lectures. Petitions demanded Harvard silence him. His name became radioactive.
Then came 1978.
At a major academic conference, as Wilson prepared to speak, a fellow academic walked up and dumped a pitcher of ice water over his head. Someone shouted that his work justified racism and oppression. Cameras clicked. The message was clear. Debate was over. Punishment had begun.
Wilson stood there soaked and silent.
He did not withdraw the book. He did not apologize. He did not trade clarity for safety. Instead, he did the one thing his critics could not stop. He kept publishing. He rewrote arguments. Added data. Clarified limits. He insisted that explaining behavior did not excuse injustice and that ignorance had never protected anyone from misuse of power.
The cost was real.
Collaborations ended. Friends distanced themselves. Grants became harder to secure. For years, “Wilson” was shorthand for controversy. But biology kept moving, and it kept moving in his direction.
Quietly, the field absorbed his ideas.
Behavioral ecology expand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merged. Conservation biology adopted his frameworks. The same academics who once shouted him down began teaching softened versions of his arguments. No apology followed. Progress rarely comes with one.
Wilson pivoted to a larger warning.
He began documenting biodiversity loss, calculating extinction rates, and arguing that humanity was dismantling the systems it depended on. He proposed protecting half the planet to preserve life itself. Once again, critics called him extreme. Once again, the math refused to care.
E. O. Wilson did not become controversial because he was careless. He became controversial because he was early. He learned what every truth-teller eventually does. Institutions forgive being wrong. They do not forgive being premature.
He was not attacked because his ideas were hateful. He was attacked because they could not be easily controlled.
-----
讀《作客雨林》金恆鑣譯; 漢清講堂141 金恆鑣博士:環境生態與文學 2017-02-18 ,簡介他的父親哥哥們: 冥若,恆偉 昭和町。
徒步旅行的書或值得一記 《作客雨林》金恆鑣譯; 《低賤血統:愛爾蘭邊境徒步行》Toward the end of 1840, Gustave Flaubert traveled in the Pyrenees and Corsica.[
作客雨林
Gustave Flaubert (UK: /ˈfloʊbɛər/ FLOH-bair, US: /floʊˈbɛər/ floh-BAIR;[1][2] French: [ɡystav flobɛʁ]; 12 December 1821 – 8 May 1880) was a French novelist. He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literary realism in his country and abroad.
He made a few acquaintances, including Victor Hugo. Toward the end of 1840, he traveled in the Pyrenees and Corsica.[
| 《低賤血統:愛爾蘭邊境徒步行》 | Bad Blood: A Walk Along the Irish Border |
東海1975年級回娘家
漢清講堂 Hanching Chung
馮睎乾十三維度
帶你到夢幻之地的小光團
「能夠跟張艾嘉、吳君如一起提名,你已經贏了!」前幾晚的飯局中,一位傳媒界前輩這樣鼓勵獲提名金馬影后的鍾雪瑩。那是「死亡組別」,對手都是享負盛名的資深演員,對年輕人來說,有份角逐已是一種勝利,鍾雪瑩大概也不敢奢望封后。可她真的做到了,簡直「雙倍得勝」,恭喜!
先來說黃修平導演的《看我今天怎麼說》,這是一齣講述聾人如何尋找和表達自己的片子,故事很有意思。片中三位青年,素恩(鍾雪瑩飾)、子信(游學修飾)和Alan(吳祉昊飾),他們都是聾人,各自有不同的理想,一邊在人生路上磕磕絆絆,一邊努力為生命配上聲音。
我日前在台北看了電影,三位演員都十分出色。其中吳祉昊是戴助聽器的聾人,第一次演戲(開鏡前上了半年戲劇課),已表現得恰到好處,令人佩服。游學修全片幾乎沒有對白,他因此學了一年手語。鍾雪瑩為了傳神模仿聾人的口語,近乎忘我地練習,有時即使沒有拍攝,也會用聾人的方式講話,常令她擔心這樣做會不會冒犯別人。
鍾雪瑩的努力沒白費。她的手語、聲音和神情,讓人渾忘這是演技,而是真實的素恩在呼吸。鍾雪瑩像一場春雨,輕輕落下,滋潤了整部片子。說到這兒,你也許會好奇,這角色她怎麼演得如此出色?畢竟她自己不是聾人。但是她懂得寂靜,所以能夠在寂靜中看到光。
她在台上說獲獎感言,表示自己曾有過不適應、動彈不得的時候,「可是內心一直有個小光團引領着我」。她想把這個獎獻給「所有感覺自己在不適應之中,在灰暗之中,每天在眼淚之中,或是身體不舒服每天來往醫院,每天在狹小房間裏仰望天空的每一位」,寄語大家「能緊握心中的小光團」,讓它「帶你到想都沒想過的夢幻之地」。
這樣夢幻的小光團,我相信是真的。想起日前看完電影後的分享會,導演黃修平提及一件趣事。幾年前,鍾雪瑩聽說黃修平想拍一部關於聾人的電影,就發了條訊息給導演,說自己也學過手語,還做過相關性質的義工。黃修平收到訊息後,沒立刻決定用她當女主角,只是把這名字存進腦海,像在心底種下一顆種子。
後來電影開拍,鍾雪瑩真的被選為女主角。拍攝期間,她有一天問導演:「為什麼是我?」黃修平笑說,是你當年發訊息給我啊。這時鍾雪瑩愣住,翻遍記憶也想不起那條訊息。人生有時候就是這麼夢幻,隨風播出去的種子,一不留神就開花結果了。
夢想,總是留給內心有光的人來實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請訂閱支持十三維度Patreon:
https://www.patreon.com/sefirot
Japanese Literature
Scott Spencer · 19小時 ·
My posting yesterday of a recent talk by Yoko Tawada about her experiences abroad reminded me of a review I wrote a few years back about one of her non-fiction works that some of her fans might find of interest, consisting of a diary concerning itself mostly with walking and writing, in which she muses about Japanese and German and everything culturally in between...https://nihongobookreview.wordpress.com/....../%E8%A8....../


孟祥森(筆名孟東籬)先生2009年9月21日病 逝台北。
「幾個月前,我決心要把我的翻譯工作結束。我不能再翻譯了,只是不能再翻譯了。我夠了,太 夠了。」(「無端」,1984年1 月,收入《野地百合》,頁51。)
----
Dear HC,
讀過孟先生「齊克果日記」、「孤獨者的獨白」,
手上還有一本他譯的海內孤本的「狂酒歌」。
既緬懷往者,也自念如何演出最後一嘗(sic 場)煙火秀。
Ken Su
*****
孟東離 草山三疊
對於「地方」,我一向是「住」而非「遊」。
如果一個地方「好」,我就會想辦法在那裡「住」下來,住個一年半載,或五年十年;在那裡生活, 在那裡起居,在那裡俯仰天地,在那裡看日出月落。
一叠:七星山東峰
這十年,我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七星山東峰。我喜歡那裡的石階坡道,那裡 無樹的芒草地,開闊,乾淨。一種蠻野的風勁,使五節芒與稀疏的樹枝都呈現著艱困環境所特有的蒼勁。我喜歡在高處臨風看整個台北市與其近郊,在那裡,你才看 到,台北市的自然環境是多麼好!幾乎是三面環山,又有三條不小的河水蜿蜒其間!
我喜歡夢 幻湖 之上,教育電台電塔之上的一段較平緩的石階路,那裡樹少草多,地形類如淺缽的缽底,而又南邊缺口,可以看到遠處的市區,總覺 那一段路是「回家的路」,甚至想在那裡蓋 一兩 間草屋,喝茶待友。
二叠:古圳
住家附近兩個讓我受惠最多的地方則是古圳與國小的校園。
古圳從我住的地方走二十分鐘,翻 過一個山坡,就可到達,圳分上中下三層,上層叫古圳,中層叫新圳,下層叫登峰圳,每一條圳都沿著圳邊有窄窄的的步道,水都清澈可飲,都來自外雙溪上游,都 可見大小不一的水潭,都可玩水,都可見魚,有時甚至可以見到蛇,甚至可以去偷摸那美麗如半透明青玉的青蛇的「屁股」——因為有時牠藏身一半就以為已經無 虞,而不想尾部還露在草外!
溪中有巨石,石上有青苔,苔下有水潭,潭中有石頭色的魚和蝦。
夏天,不論台北市區多熱,你到潭邊樹下,坐 在大石上,仍會有微微涼意。你聽到的只有水聲、蛙聲,鳥聲和偶來的人聲。
三叠:山區國小的校園
經由朋友的幫忙,在汽車不能到的巷弄,找到了一戶小小的磚石農宅。這農宅,就在國小校園後門的外邊,步行 不用一分鐘,就可進入校園。走進校園第一個視線往往就是校舍之上天空之下那遠遠的大屯山脈,有時呈翠綠,有時呈灰藍,有時飄在濛濛雨幕中,有時則為雲霧所 掩。校舍南邊,是一片平整的草地,環以磚色的橢圓跑道。在草地靠後門的這一邊,是一方水泥籃球場。
校園的周圍,幾乎盡是高大的樹木,在校園的東 南角,可以越過樹梢,看到晨起沐浴在陽光中的七星山東峰。
這樣一個校園,就是我幾乎每日徘徊的地方。
晨起,如果還沒有超過七點半,我 第一個衝動或念頭,就是到校園看看。看看那裡的花,那裡的樹,那裡的鳥,那裡的蝴蝶,那裡的蛛網,那裡的松鼠,或松鼠在樹上留下的齒痕,看看那裡的陽光或 雨霧。
或跟 那裡的 老師、校長、小朋友,打個招呼。一天又開始了。
如果我起得晚一些,就會聽到小朋友在籃 球場拍球的聲音,會聽到只有兒童才會發出的那種喧鬧嘻笑的聲音,或小朋友從我窗外走過,去上學的聲音,有一種特別的寬慰。
下午三點半,小朋友放 學了,又是我可以自由徘徊的時間。陰雨天,我在校舍的走廊下來回走路,甩手或慢跑;不下雨的日子,改在跑道。
朋友來了,帶著到校園散步,聊天或 喝茶,而有時自己也端著一杯茶或咖啡,到校園樹下小坐。甚至蒙師生、校長的寬待,可以讓我搬個藤椅,坐在校園樹下看書、發呆、喝茶,還戲稱我可以是學校的 一景。
入夜以後,如果不是盛夏,也不是寒冬,我有時就會在校舍東邊的木製平台上或南邊的籃球場上躺臥。木製平台邊有糾結的大榕樹,我躺在樹邊發 呆,往往會看到相當大的蝙蝠低空飛過。
在籃球場上躺臥的次數較多,因為此處視野開闊,周圍是透著遠處燈光的大樹,大樹之間圍成的天際,可以觀星待 月。地處台北近郊的山區,雖然很少繁星燦亮,但有星可看,已屬慶幸,而月亮不論盈缺,則常現清輝。
入夜的校園,幾乎無人,唯我獨享。有時也有友 人相伴,常在身邊的則往往是 一兩 隻毛色黑亮的台灣犬。
這幾年的山居,使我覺得,郊區迷你國小的校園有特殊的宜人之處,我甚至想,如果將來再搬 家,還要選類似這樣的國小旁邊,怡吾天年。
*****
人有時候免不了會問自己所做、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很重要、很有價值嗎?如果夠誠實,你會想到,如果此刻世界失去了你,也沒有什麼損失。這個時候,你大概會有空空的感覺,好像變成一個氣球,向空中飄去。也許就這樣一去不返了。但是,你如果有小孩,就不會這樣隨便飄走。很難講是為什麼。不一定只是為了照顧他,甚至也不止是為了給他經濟上的支援。因為你並不認為,如果你給他留下一筆錢,就可以放心無愧地去了。你好像跟他訂了什麼契約似的,覺得他在幼小的時候不能沒有你。說得好聽一些,就是你的存在有了價值,至少對某個小孩來說,你很重要。社會可能不需要你,但是你的小孩卻像根釘子,把你釘在生活上,不讓你隨便飄去。-----孟東籬《人間素美》,收入《讀者文摘‧意林》1998年4月號
“The world reveals itself to those who travel on foot.”
【不甘只做新聞配圖的記者──林國彰以蹲點發揮紀實之眼的「老派」攝影道】https://pse.is/5w97qt
出身《中國時報》攝影組,林國彰在台灣社會解嚴、報禁解除的媒體競爭時代入行,當時具有社會意識的圖文報導與報導攝影正興起。
信奉以長時間蹲點紀實的老派攝影之道,林國彰在不同新聞現場、拍照發稿的忙碌日常中,犧牲假期完成少量專題。過去最有計畫性的專題拍攝都與痲瘋議題相關,為中國涼山與台灣樂生留下深刻的攝影作品。
近期出版的《臺北道》,是他入行40幾年第一本攝影集,匯聚了他10年來的生活與觀察,也是對自己身處城市的深遠凝望。對於攝影中所隱喻的歷史感,林國彰說:
「我能夠做什麼?我不知道能夠做什麼。我就只是拍下那個當下,然後放著過了10年、20年,讓另外一張照片來取代它。透過不同階段的照片,你就可以看到歷史。⋯⋯而我,只有這個拍下來的動作,沒有其他了。」
★提供觀點,促進思辨,#贊助報導者:https://bit.ly/2Ef3Xfh
無影無蹤全州影展第一天,目睹蔡明亮導演在全州舉辦的「《行者》表演大賽」。
.
昨天晚上經過全州的電影街,發現前面鋪了一個紅毯,圍觀者眾,走過去發現一群人以行者的姿態(創作概念是取自前往西天取經的僧侶玄奘)在紅毯上行走,蔡導則在旁舉起相機紀錄過程。參與人數大概有十幾個人,而且都有各自的造型,例如有人身穿白衣用紅線跟另一個人綑綁在一起行走。昨晚我也即時分享了現場拍攝的影片,請見上一篇發文。
.
後來查閱新聞才知,這不只是一般的粉絲活動,而是蔡明亮導演舉辦的「《行者》表演大賽」。依據韓國媒體報導,這個比賽最初的構想是要將最大獎頒給走最慢的人,不過蔡導最後覺得每個參賽者都讓他很感動,所以改成通通有獎,每個參賽者都可以獲得他準備的咖啡等禮品。
蔡導表示:「原本以為他們(指參賽者)會像電影裡的行走一樣行走,但是他們最後都按照自己的步伐來行走,讓我很印象深刻。所有人的姿態都不同,速度和姿勢也不同,都非常漂亮。」
非常佩服全州影展的創意呀,才第一天就讓人驚艷。其實不只是蔡導的「《行者》表演大賽」,昨晚還有料理烹飪課程,邀請影人一起在料理教室學習做韓式拌飯,這也是我從來沒有想到影展能夠做到的企劃。這就是為什麼比起去這些高大上的影展,我更喜歡去小城小鎮的影展,總是會有很多啟發性。
最後,敲碗「《行者》表演大賽」也能夠在台灣舉辦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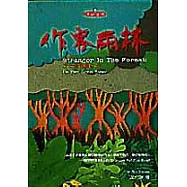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