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勞思光先生九十八歲誕辰(1927年9月3日),
勞先生的學生維晴特別幫勞先生準備的早餐和咖啡,
這是勞老師生前來學校時,習慣吃的早餐(火腿、蛋、吐司),
再過兩年就是勞先生百歲誕辰,
正在構思該怎樣來辦紀念他的百歲活動!
WIKIPEDIA
勞思光(1927年9月3日—2012年10月21日),原名勞榮瑋,字仲瓊,號韋齋,筆名思光,湖南長沙人,中國哲學家及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生平
家庭及成長
勞思光是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人,出身翰林世家,打下紮實深厚的國學基礎。
高中畢業,勞思光至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未及畢業,就因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遂隨父母移居台灣,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完成學業。其後的白色恐怖年代,因反對國民黨獨裁,主張民主自由,引起調查局與警備總部注意,意圖加害,得其父舊部通知危險,被迫離開台灣,寓居香港。
勞教授反對專制,發誓除非共產黨下台,否則不回中國大陸;又發誓除非台灣解嚴,否則不到台灣,所以勞師下半生從未踏足中國大陸,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勞師的著作都被台灣政府列為禁書,甚至父母過世,也無法返台奔喪。[1]
香港時期
勞教授到港後,專心在學術方面,先後於珠海書院、崇基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哲學,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勞教授在中大崇基學院時,除任課之外,尚須編寫教材,譬如勞教授就因此而完成《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後來他更擔任研究所主任一職。勞教授公務雖忙,但著作更勤,特別以《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名重於時。但勞教授也非常關心時局世運、重視中國前途,於是在1981年請李怡等共同發起組織「前景社」,探討香港及中國的前途。勞教授退休後,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該校逸夫書院高級導師。
勞思光在香港中文大學授課期間,與唐君毅、牟宗三齊名,被喻為「香港人文三老」。其所著的《新編中國哲學史》,運用其提倡的「基源問題研究法」進行嚴格的分析,展示中國哲學各時代不同門派的學術見解與內層理境,出版以來,深為學界所重,有學者推重之為同類型著作之中最突出的一本。
臺灣歲月
勞教授離台前,曾立誓說除非國民黨終止戒嚴,否則不回台灣,並時常關切、幫助台灣的黨外運動。從香港退休後,因為台灣已經解嚴,1989年年勞教授受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亦園之邀,擔任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在台期間,勞教授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及華梵大學,擔任華梵大學教授及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並於2001年榮獲台灣行政院文化獎,2002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勞教授在台,仍然不改關心時事的心懷,除了應邀撰寫報紙短文外,1990年代民進黨人士接觸勞師,勞教授點出民進黨不能只以反對國民黨而自足,而應該對兩岸問題及台灣前景提出正面的方案,此後,民進黨人士草就《台灣前途決議文》。2005年,勞教授以七十八高齡,仍關心時事,倡議反對六千億元新台幣的軍購案,與其他十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聯名發表建言,終於力挽狂瀾。勞教授晚年多病,癆病未癒,外加腸胃病,讓身體虛弱,常常感冒,2010年,勞教授因大腸癌,入院進行切除手術,當時馬英九總統曾親自去醫院探訪。
詩稿| 勞思光先生存稿整編

主頁 >
詩稿 >
居港時期 >
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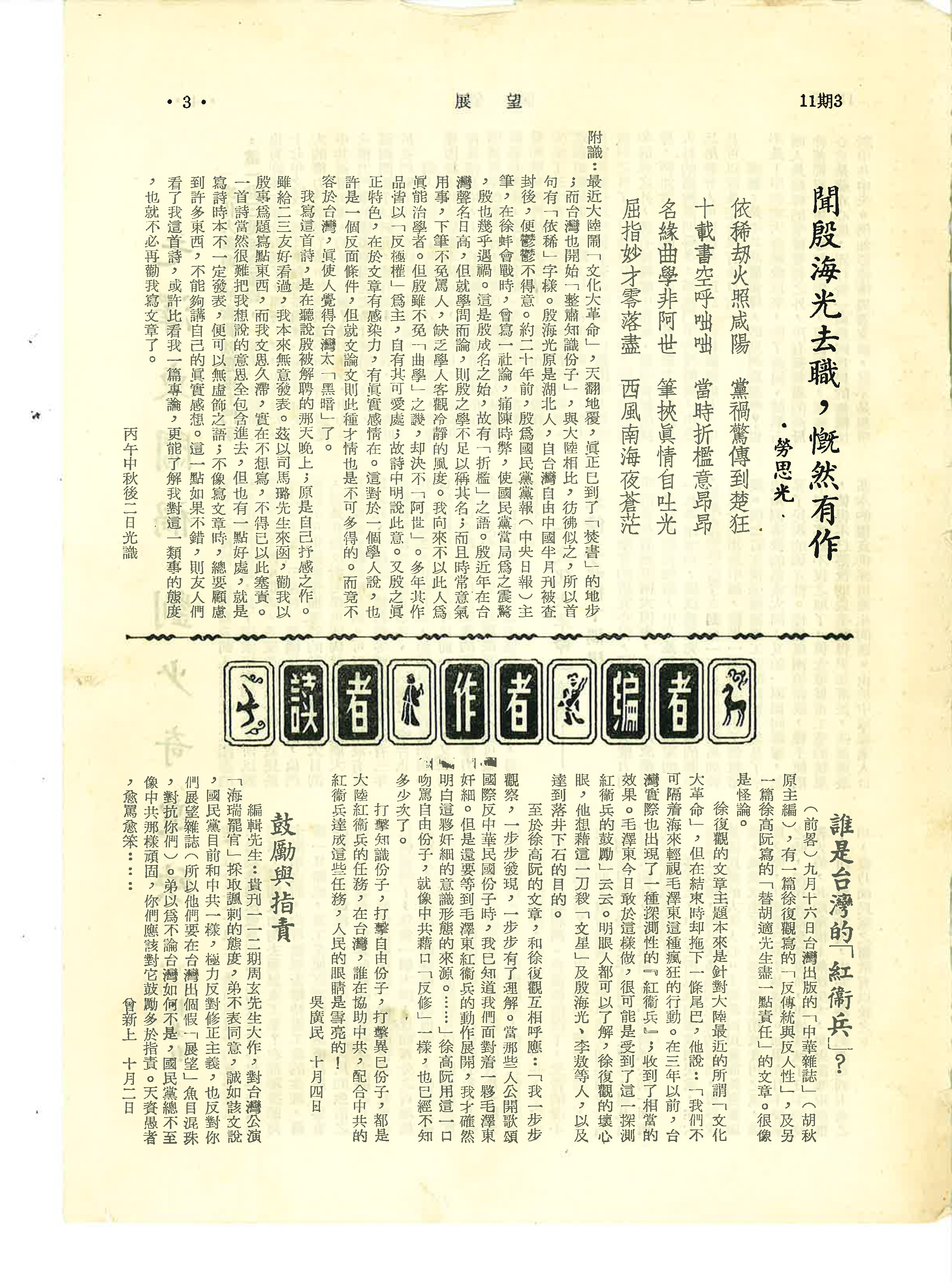 |
| | 編號 : | poem_015 |
| | 標題 : | 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 |
| | 年份 : | 丙午 (1966) |
| | 內文 : | 依稀劫火照咸陽,黨禍驚傳到楚狂。
十載書空呼咄咄,當時折檻意昂昂。
名緣曲學非阿世,筆挾真情自吐光。
屈指妙才零落盡,西風南海夜蒼茫。
附識: 最近大陸鬧「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真正巳到了「焚書」的地步;而台灣也開始「整肅知議份子」,與大陸相比,彷彿似之,所以首句有「依稀」字樣。殷海光原是湖北人,自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被查封後,便鬱鬱不得意。約二十年前,殷為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主筆,在徐畔會戰時,曾寫一社論,痛陳時弊,使國民黨當局為之震驚,殷也幾乎遇禍。這是殷成名之始,故有「折檻」之語。殷近年在台灣聲名日高,但就學問而論,則殷之學不足以稱其名﹔而且時常意氣用事,下筆不免罵人,缺乏學人客觀冷靜的風度。我向來不以此人為真能治學者。但殷雖不免「曲學」之譏,卻決不「阿世」。多年其作品皆以「反極權」為主,自有其可愛處;故詩中明說此意。又殷之真正特色,在於文章有感染力,有真實感情在。這對於一個學人說,也許是一個反面條件,但就文論文則此種才情也是不可多得的。而竟不容於台灣,真使人覺得台灣太「黑暗」了。
我寫這首詩,是在聽說殷被解聘的那天晚上;原是自己抒感之作。雖給二三友好看過,我本來無意發表。茲以司馬璐先生來函,勸我以殷事為題寫點東西,而我文思久滯,實在不想寫,不得已以此塞責。一首詩當然很難把我想說的意思全包含進去,但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寫詩時本不一定發表,便可以無虛飾之語;不像寫文章時,總要顧慮到許多東西,不能夠講自己的真實感想。這一點如果不錯,則友人們看了我這首詩,或許比看我一篇專論,更能了解我對這一類事的態度,也就不必再勸我寫文章了。
丙午中秋後二日光識。 |
| | 刊行本 : | 《思光詩選〉頁57;
《述解新編》頁156,編號93〈聞殷海光解職,慨然有作〉 |
| | 相關詩稿 : | poem_131〈聞殷海光解職,慨然有作〉;
poem_206〈聞殷海光解職,慨然有作〉 |
| | 備註 : | 編按:右上「11期3」是113期之誤植,《展望》113期於1966年10月16日出版。《展望》雜誌由司馬璐創辦,第一期於1958年4月1日出版,初為月刊,於1965年4月(總第76期)開始改為半月刊。
勞先生於香港「新民報」〈苦語〉專欄中有一篇「憶殷海光—懷友篇之一」(~1963–64),可與之比讀(見「勞思光研究中心」facebook 專頁 (11 Mar 2024):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2AKqkFfPa7kPMW93ZVKrMBH96Db6ZzQUph8GZ82PZGuykLi2Go47k4F3P8eVbxSERl&id=100057430060825。
|
韋齋隨筆_疲憊的危機
近來為一件事忙碌了一個星期,竟然大感疲憊。默坐養神,忽然領悟到疲憊也含有一種危機。
疲憊的人自然需要養息,但能否養息却要受客觀環境的限制;疲態憊而不得養、不能息,則活力無法恢復,危機隨之而至。個人求養息,或許尙容易辦到;一個國家能否養息,却常常是一個複雜問題。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一向鬥來鬥去;到了文革時期,全國人民更是在瘋子的領導下一面亂殺亂打,一面到處破壞。中國整個國家,眞可說是「甚矣憊」!現在瘋子不再領導了,可是,疲憊的大陸能够 真正獲得安養休息的機會嗎?
要國家能安養休息,需要許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秩序與政治自由。文革後的大陸像一所殘破的大屋,必須先作一番修補,然後纔可能讓人在那裏休息。最近,鄧小平一派推行他們的改革,先有了農村的責任制,又建立了經濟特區;再加上改革價格制度,似乎喚起了社會活力;但是,經濟生活的局部改善,却未必眞表示疲憊的中國已經蘇復。
如果我們冷靜地視察近兩年大陸社會的實際變化,很容易看出來經濟管制的放寬,並未觸及社會病根所在。文革後的大陸,不僅物質生活方面疲憊不堪,而且理想性消失,精神活力呈現極大的疲憊。這種疲憊,有些人也許認為是「好事」——因為這表示馬列主義的教條已經逐漸喪失力量,但是,實際上這種疲憊正隱藏著社會性的精神崩潰的危機。這裏的病根不除,則表面上經濟的改善,適為貪污舞弊者所利用。實例已經很多,不待多說。
精神活力的疲憊,只有在法治秩序和自由思想的環境下,方能逐漸消去。中共當局在這方面能作多少努力,却是未知之數。
(本文歡迎分享)
「自古至今,多少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生命。這些人在當時不是曾被咬定為叛徒?然而,時過境遷,那些咬這些志士為叛徒的人們,卻替歷史留下了人類自私、愚蠢和黑暗的紀錄。」
莊文瑞殷海光教授晚年被禁上課和發表言論,卻在美國支持下完成研究計畫分析“國民黨的本質”論文,是了解國民黨不可或缺的最佳史料之一。我在大二轉哲學系,就是高中導師在高三送了我“思想與方法”一書,害我一輩子中了哲學的毒,尤其是自由主義特別嚴重。哈哈,感謝高中導師,更感激殷教授的哲學啟蒙,也為自己再承傳這些哲學思想與精神而高興和欣慰。當然,最要謝謝筱峰的努力與認真!
幾年前有一位在香港某出版社負責的朋友,偶然和我閒談,提起台灣青年的思想方向;他說:「現在海光影響力之大,遠非從前可比了。」那時候自由中國半月刋尚未遭查封,我有時也看看殷海光在那裡發表的言論;我對他的印象沒有多大改變,但我聽說他能夠影響台灣青年的思想,仍是爲他欣慰。
殷海光的氣質,應算是有政治熱情的文人;但他却偏偏學邏輯,邏輯家所需要的平靜與超越感,他一點都不具備。他提筆寫文或開口講話,永遠是情緒激動非常的;他之能得青年擁護,固是由於這種「熱情」。他在哲學與邏輯研究方面未能大成,也是受了這種氣質的限制。
我第一次聽見「殷福生」反對國民黨,是在徐蚌會戰以後。那時候我在北平,劉思恭告訴我「殷福生」爲中央日報寫了一篇社論,惹下禍事。後來我找到了那篇文章看,題目是「趕快收拾人心」,這篇文章雖然抨擊政府失策,有很多地方可算「直言」,但基本上仍是站在國民黨立場說話;誰知道竟成爲殷海光與國民黨决裂的決定因素呢? 殷海光在思想上贊成民主政治, 似乎是後來的事。許多老朋友都知道他在西南聯大很有崇拜英雄的想法。對德國的希特勒,他并不怎樣反對;甚至對於中國當時的獨裁領袖蔣介石,也還寄予希望。等到他參加了國民黨,與二陳及陶希聖十分接近以後 ,他反而漸漸了解國民黨前途大成問題。同時,他思想也有轉變。在台灣,我見著他的時候,他已是一個很急進的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同時他與國民黨的關係也愈來愈疏遠了。
殷海光的中文不算好,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他學了邏輯解析,走上維也納學派路線,更是西方形上學與價值哲學都全盤否定,對中國的心性之學,更是非常反對。但因為他看中國書實在太少,批評起來每有用語不當或根本誤解原意之處,所以,他和人談起中國文化思想來,總是鬧得非常不愉快。別人覺得他實在不大懂,信口亂說;他則覺得别人思想落伍,是可鄙視的。很少看見他和人辯論,能彼此有所增益。祇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很缺乏哲學家的氣質了。
我在台北,有一段時間與他常常見面,談一些思想問題;雖然不完全相投,也不曾有甚麼衝突。有一天,我在衡陽街散步,碰見了;我們同走了一條街;一面閒談,我向他說:「你是作邏輯工作的人;你又反對一切絕對性的判斷;爲甚麼你老是以一種獨斷口吻評論一切呢?」他聽了, 似乎很不好意思,祇說 :「并不獨斷」。我也就沒再談下去。其實,我對他說的這一句話,倒是眞心話。凡是稍有思考訓練,了解知識的結構的人們,都明白人人的所知所見,皆不能實現「絕對性」;所以,稍有教養的人,决不自命爲代表眞理。只有無知而愚昧的人,纔會自以爲代表眞理說話。愈是學養深的人,愈知道一切問題都不能看得太簡單;也愈能有虛懷求進步的風度。殷海光本有這種知識,不致於陷入小觀念網中不能自拔 ;但他的氣質是偏於縱情任性一面, 所以,常常表現得很獨斷,近年為聽說他又有進步,或許已經不像從前了。
殷海光在「自由中國」寫稿時, 曾爲了一篇評論金岳霖的文章,而寫文大罵了我一次。其後,我再未見過他。他之罵我,自然在我情緒上也造成一種不快;不過他的可愛處、可佩處,我仍然完全承認。至於他的缺點,則除了上面提的「獨斷」以外,還有一點,就的:他永遠喜歡用刻薄輕浮的筆調談莊嚴問題。影響是很壞的。不久以前,我看見台灣的「文星雜誌」,上面幾篇東西都是學他的路數寫的。足見他影響台灣青年是事實,而他的毛病也真傳給青年們了。有人以為现在需要大罵和打架,我則覺得打架罵人中決不會有進步,殷海光今日不知如何看法。
(本文歡迎分享)
話說當年時空環境下,殷海光先生這番話,其實是有遷怒的味道在,對於推動黨國體制的教育這回事,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控制,我想除非殷海光先生不知道前三青團臺灣支團的團長李友邦先生是怎麼死的?我想他說這樣子話,不是心眼小?就是腦子好?免得自己的腦袋和脖子分開了!~
_____
張其昀在臺灣擔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期間,促成多所大學的在臺復校和新學校、學系的建立,開創博士學位教育,著力中小學基礎義務教育,奠定了臺灣的教育格局,也促進了台灣地理學的發展。期間將當時南海學園規模大幅擴張成為「南海五館」,亦即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等,並於1955年在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成立了地理學系(今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1958年7月,陳誠組閣,由梅貽琦出任教育部長。當時殷海光即於《自由中國》十九卷發表〈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稱「其中最得人心的決定,是把前任教育部長換掉了。前任教育部長之換掉,教育學術界凡屬稍明事理的人士,無不額手稱慶,無不稍微鬆了一口氣,無不對自由中國教育的前途寄予一點新希望。」殷海光更在文中批評「前任教育部長」的四大作風為「個人創霸」(利用職權的便利和公家的金錢創辦一些品質低劣的刊物,雇用小嘍囉來自我歌頌)、「好大喜功」(樹立機構如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藝術館等,只有形式而無內容)、「政教不分」(對「黨化教育」雷厲風行,在學校灌輸青年部族思想)、公私不分(毫無國家體制、法令,將原有編制七十人的教育部擴充為三百人,把大筆教育經費撥給他私人所主持的出版機構訂購書刊)。認為撤換教育部長是「教育界的剋星已去」
《美育之新發展》 民國44年10月31日-國立藝術學校成立典禮致詞
今天我們在台北縣板橋公園舉行國立藝術學校成立典禮,設想後世寫中興建國歷史的人,或許會把這裡看做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塊沃土。我們現正開播種與耕耘,確信將來終會開著燦爛之花,結著美滿之果,這便是我們深相策勉,共同努力的目標板橋林氏園林之盛,世所豔稱,是園建於咸豐三年(1853),為寶島勝蹟之一,在百週紀念之後,而有新公園之建設,可謂前有輝,後有光了。
我們計畫在臺北市區和郊外,建設兩個文化中心,在市區是植物園的東首,在郊外就是這裡板橋公園。在植物園東首我們要建設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國立台灣科學館,和國立台灣藝術館。在這裡板橋公園要建設國立藝術學校,國立華僑中學,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電影製片廠,科學儀器造廠,及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等。這些機構,有些是恢復,有些新建,都是互相關連,而為中國文藝復興必須的礎石,我們深信假以時日,上述理想,定能逐漸實現,又當使市區和郊外兩個文化中心,收到左右逢源,相得益彰之功效。
真正的文藝復興,必以培養人才為先急之務。國立藝術學校的內容,就程度言,包括高級中學與專科學校二個階段。就學科研,包括音樂,繪畫,建築,雕刻,戲劇,舞蹈,電影,及美術工藝諸部門。本學期先創辦高中程度三學科,即中國歌劇,話劇,與美術印刷三科,每科各招新生四十名,共一百二十名,今天全校師生相聚一堂,在 總統華誕的吉日良辰,同時慶祝本校的誕生,實在是極有意義的事了。張其昀於1955年10月31日,在國立藝術學校成立典禮致辭中談到《美育的新發展中,他認為國立藝術學校的成立,是藝術界、也是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塊沃土:美育的發展正開始播種與耘,確信將來我們在藝術上會有美滿的結果;也更希望國人可以深相策勉、共同為藝術努利。
本校教育宗旨,完全依據 總統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指示,力謀美育之新發展,美是什麼?它就是人生的寫真,壯美優美兩者應兼而有之。質言之,美是生活的精萃,與生命的創造。美之理想,是快樂,是幸福,所謂自尋樂趣,自求多福。美與仁愛,息息相通,美可說是心之德,愛之理。美之功效,應該是世道人心的啟發,也是國利民福的實踐。美之為德,乃是樂觀進取,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生生不已的,它是充滿於宇宙,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和諧而有秩序的,易言之,它是瀰漫於空間,貫徹於時間,為全民所共享,歷久而常新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境,和足以稱之為美?「廄有肥馬,野有餓莩」的情景,更何足稱之為美?美不是遺世獨立的,必須真善美三者合為一體,美善相樂,仁智雙修,禮樂交融,斯為進德修業之極致。準此言之,我們必須具有先憂後樂的精神,天下為公的懷抱,光風霽月的胸襟,民胞物與的雅量,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理想,臻於實現,這才是美宗旨。
電化教育的實施,是教育上之大發明,也是教育上之大革命。電化教育包括廣播,電影,與視聽教育等,而電影尤可稱為綜合藝術。文學與藝術創作,至電影而集大成。我們國立藝術學校各種學科,各有其意義與價值,而電影一門,則取精用宏,實為畫龍點睛之所在。本人希望明年度本校添設專科程度的影劇編導科,以培養電影之編劇導演人才,其他各科當再徐圖擴充。
教育電影製片廠,負有製片之任務。國立臺灣藝術館,則為音樂戲劇舞蹈與電影經常表演,映演與訓練之場所。希望將來能夠左提又挈,密切連繫配合。教育部行將設立國產電影輔導委員會,更望期能集中力量,為電影事業厚植其基礎。現代藝術之發展,真可謂有聲有色,其入人愈深,而化人愈速。要之電化教育堪稱為教育上之原子武器,其影響之深鉅與普遍,誠為空前所未有。際茲原子時代,而創立私校,我們必須「商量舊學,涵養新之」,好學深思,真知力踐,以期不負於這偉大的中興時期所賦予我們的任務和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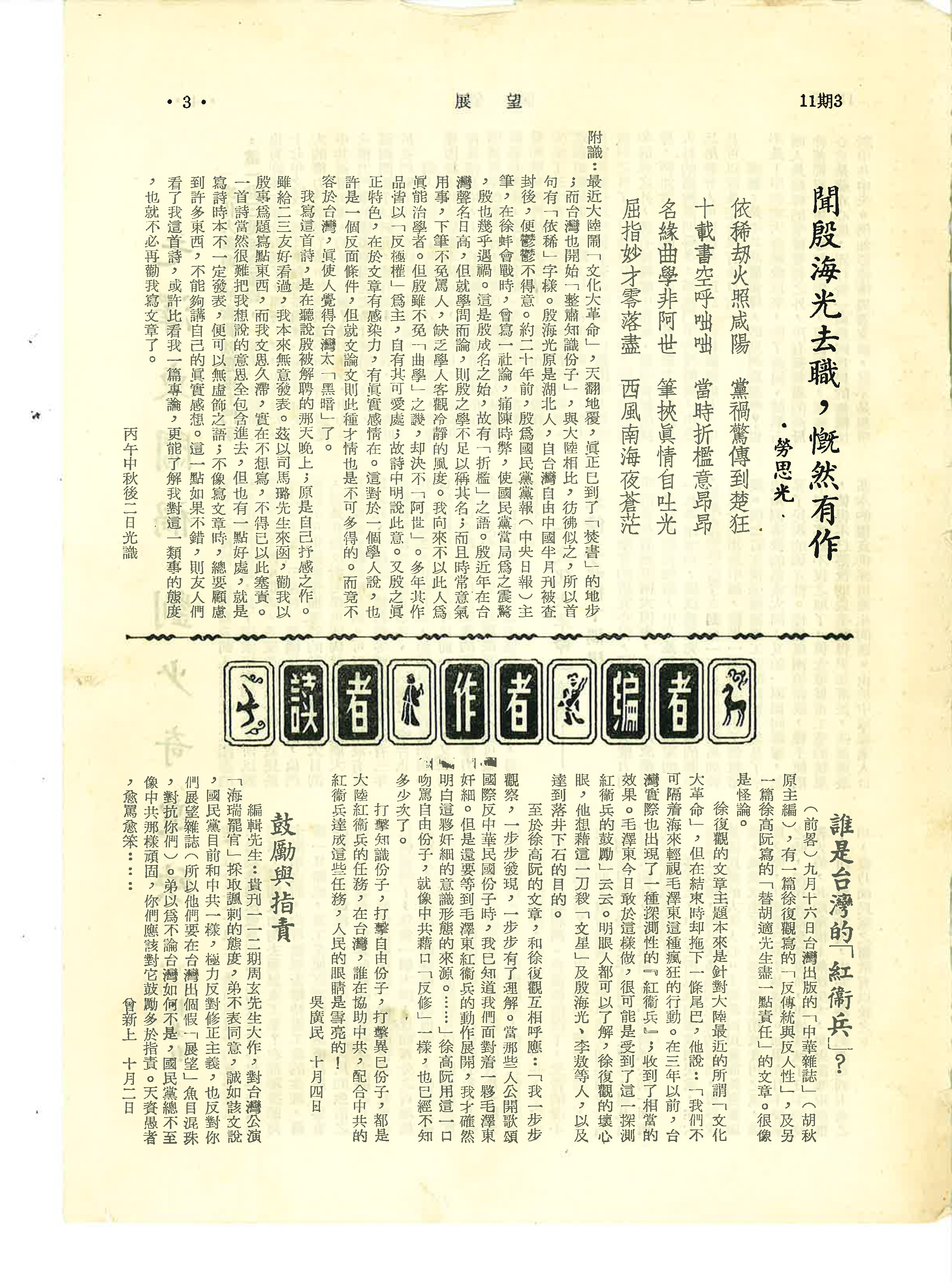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