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國發動大膽突襲,逮捕委內瑞拉獨裁者尼古拉斯馬杜羅幾天后,他領導的政權似乎正在迅速恢復正常。Just days after a daring raid by America that seized Venezuela’s dictator, Nicolás Maduro, the regime he led appears to be righting itself rapidly
//獨裁聯盟遭受重挫更關鍵的是,獨裁者賴以為生的聯盟正在鬆動。俄羅斯深陷戰爭消耗,中國自身經濟下行、內部焦慮升高,已難再無限為他國政權兜底。當保護傘破裂,獨裁者便赤裸地暴露在民意與現實之前。所謂「主權」若只用來保護統治者,而非人民自由,終將失去正當性。歷史反覆證明,國家不等於掌權者,穩定也不等於壓迫的延續。真正摧毀國家的,從來不是外力,而是專制、腐敗與對人民尊嚴的系統性踐踏。當人民拒絕再充當工具,威權互保的神話就會瓦解。獨裁聯盟今日所遭受的重挫,正是這個時代給出的清晰警訊。下一個倒台的是誰?//
------
在《破碎的中國夢》一書中,裴敏欣揭開了強人習近平政權的神秘面紗,揭示了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為何幾乎在所有領域都遭遇逆轉,以及世界為何未能預見這一趨勢。
本書現已上市(英國1月27日出版)。閱讀本書免費試讀章節:https://hubs.ly/Q03YCN1N0
When China embarked on its transformative journey of modernization in 1979, many believed the country’s turn toward capitalism would put its totalitarian past to rest and mark the birth of a democratic, open society. Instead, China reverted to a neo-totalitarian state, one backed by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most formidable economies on earth. The Broken China Dream pulls back the curtain on the regime of strongman Xi Jinping, revealing why the reforms of the post-Mao era have been reversed on nearly every front—and why the world failed to see it coming.
Exposing the truth behind China’s economic ascenden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nxin Pei shows how, following Mao’s death in 1976, Deng Xiaoping strategically deployed the tools of capitalism to pre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ng kept intact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otalitarianism even as he unleashed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courted foreign investment, giving China’s one-party state control of a vast repressive apparatus and the most critical sectors of the economy. Only a fragil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dueling factions prevented the rise of a totalitarian leader in the two decades after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in 1989—but this temporary equilibrium collapsed.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oday’s China, this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book is a sobering account of why the country’s reformers and institutions could not stop a shrewd and ruthless politician like Xi from resurrecting dormant totalitarian practices tha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have spelled the end of the dream of a free and prosperous China.
Contents
| 15 |
| 45 |
| 74 |
| 101 |
| 132 |
| 146 |
| 164 |
| 192 |
| 222 |
| 253 |
| 261 |
| 291 |
| 305 |
| 311 |
| 319 |
Common terms and phrases
作者簡介
康正果
西安人,現居美國康州。已出版的著作有《出中國記》、《肉像與紙 韻》、《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和《平庸的惡》等書。
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目錄
有位朋友曾寫信對我說:「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為世界和人類文化服務的層面上,俄國人交出了史達林,德國人交出了希特勒。」接著他大發感慨,為中國人不但沒交出毛澤東,還把毛當作民族的驕傲以示人的現狀而深感失望。我回信告訴友人:「確切地說,並不是中國人至今還不交出毛澤東,而是中共不准中國人民交出毛澤東,是中共不願意,也不敢交出,交出毛澤東就等於交出了他們自己。」中共集團與毛澤東相依為命,毛身雖死,毛魂猶活,其陰影至今仍籠罩華夏大地,更擴散到海峽這邊的人群中。所以要批共就必須同時批毛,要揭示中共反國家、反民族和反人類的本質,應首先從清算毛的罪行入手。
在辨認毛共本質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只受黨化教育的大陸居民盲點深重,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不少海外華人也都是認識很模糊的。前不久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親民黨領袖宋楚瑜出面祝賀,他當場竟背誦毛澤東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與柯相勉,而柯市長居然也竪起大拇指,開懷笑納。從今日台灣民眾「去中國化」和建樹「台灣主體性」兩點最基本的國民意識出發來看這個問題,竊以為,宋楚瑜在媒體聚光燈下背誦毛澤東詩詞,那種作秀的行動本身就有政治不正確之嫌。然而台灣媒體竟予以容忍,並未見發出多少嚴正的批評言論。由此可見今日台灣輿論的反共意識疏忽麻痹之深。對於藍綠兩不自覺地回歸著善緣。」
那部回憶錄出版後,我隨即在批共評毛的課題上努力補課,決心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時期,紮實修煉我推進善緣的「正動」能量。我開始大量閱讀毛澤東著作以及與毛和中共黨史相關的書籍文章,特別是讀到像張國燾、龔楚等與毛澤東共處過的中共高層人物所著紀實回憶之作,始得以阿凡達一樣穿越歷史迷霧,加入到他人的經歷中近距離感知毛澤東在價值階序上的低劣原貌。
本書既非為毛澤東立傳,也非中共黨史模式的編年敘事,而是將毛澤東其人其事及其文置於中共自成立到武裝奪權成功的脈絡中夾敘夾議,做出應有的歷史審判,為必須伸張的轉型正義提供一連串嚴正的證詞。原稿的敘述終止於內戰結束,後來接受出版社主編廖志峰先生建議,我又特別補寫最後一章,一口氣縷述了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禍國殃民的史實。在此我首先要對廖志峰表示感謝,是他的建議促使我寫成足以與本書正文部分相映成趣,形成強烈呼應的結語,從而突顯出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發生的重大變異。我就此也便把批共評毛的書寫告一段落,算是給讀者做出了完整的交代。
身為一普通的中文教師,本人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作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院學養,更不擁有解密檔案或得自當事人談話的珍稀資料。寫這部敘事與議論摻雜的厚書,我無意在史料發掘上出奇取勝,而只滿足於從已經面世的史料中勾勒線索,搔到癢處,做些舉一反三和點到即止的工作。歷史意識的覺醒如今在大陸已遍及民間,從體制外和非學院立場上批共評毛的作者群日益壯大,中共不交出毛澤東的禁錮現狀正在被堅決要交出毛澤東的民間人士分段拆除,逐步突破。在撰寫此書過程中,我特別借重了幾位五〇、六〇後一代作者的著作,其中有堅守在體制外,埋頭作獨立研究的蘆笛、陳小雅和顧則徐,還有人在學院內教書,卻敢於摒棄官方話語的高華、單少傑和楊奎松,他們的研究成果使我獲益良多。
老友周劍岐更是我要在此加倍感謝的重量級人物。讀者若讀過我《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一書,當會對周君的思想及論述留有印象。周君經常通過電郵傳給我他在網上發現的資料,還借給我他自費購買的書籍。我寫稿中有所疑難,停滯不前時,他及時開導疏通我的思路。我每完成一章,他總會及時閱讀初稿,提出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埋頭寫稿的三年歲月中,若無周君一再鞭策,我很可能會在寫作中途氣餒而輟筆。通過電話和電郵互相交流,周君可謂自始至終地參與了我這部書稿的寫作。
我還要感謝友人胡平和台灣政大的陳永發教授為本書撰寫導讀序言。在深入瞭解中共黨史以及毛澤東其人其文的閱讀方面,兩位學者的有關論述均對我有不少啟發。我自 1994 年移居美國即訂閱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可以說自從那時起,該刊上登出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胡平的文章,都影響到我寫這部書的思路。陳永發所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史實詳盡,敘述縝密,也是我寫稿過程中一直參照的歷史坐標。
我最後要感謝耶魯大學東亞系的領導及各位教授在我退休時授予我榮休(emeritus)待遇,這待遇使我在退休後能享有與在職教員同等的借書特權。如果沒有耶魯圖書館東亞部豐富的收藏供我盡量參閱,我這個「還原毛共」的工程根本就無從下手。我同時還要感謝耶魯東亞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一直資助我從事共產文化研究的豐厚經費,使我得以到台灣查找和購求所需的大量書籍。
隨著讀網者日增,讀書者日減,台灣書籍出版業的營銷也日益艱難,經營者在出版選擇上大都偏重市場效果。再加上中共方面的出資收買和文化滲透,島內的不少書商在涉及大陸的敏感問題上便顯得膽小怕事,也幹起了自我審查的操作。像允晨文化這樣不太過份計較收益,更不在乎中共當局好惡,而始終堅持其出版原則的出版社已越來越少了。我因此要再次感謝廖志峰及其他相關的主管人士。
康正果:蘇曉康「非毛化」觀點完整詳解
【按:我曾有言:「康正果是我的同龄人,其著作《还原毛共》,继承前辈遗绪,且拓深并细化,在今日中文话语中,堪称空谷足音。」然而我未曾想到,我們還是當代「非毛化」的罕見、寂寞同路人,今見正果此文,極感慨他的細膩梳理,乃是對我書寫中三十年不眠不休一脈話語的第一次彰顯,讀來令我一驚,而有幸獲得「落寞身姿孤島心,頂天立地到如今」的當今獨樹一幟文評家、並獲余英時「人生識字憂患始」讚譽的康正果評論,何其有幸。並附《光棍、枭雄、混世魔王》。】
蘇曉康是當代中國最堅定、最系統提出「非毛化」理論的思想者與寫作者。他從1980年代末開始,至今超過35年,從未改變立場,也從未妥協。他的「非毛化」主張可歸納為以下十大核心觀點,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完整的政治-歷史-文化清算理論。
1. 非毛化是中國現代化的絕對前提。
——「不徹底非毛化,中國就沒有現代化可言。」這是他最著名的一句話(1989年起反覆講)。他認為毛澤東路線的本質是「反現代化」:反市場、反法治、反個人權利、反普世價值。只要毛的意識形態遺產(黨國體制、個人崇拜、階級鬥爭論)還在,中國的一切改革都只是「假現代化」,遲早會倒退。
2. 「非毛化」不等於「反毛」,而是「去毛毒」
——蘇曉康刻意把「非毛化」與「反毛」區分開來:
• 反毛是情緒宣洩、推倒銅像、挖墳鞭屍
• 非毛化是制度性、法律性、歷史性的全面清算——他借用東歐「去共產化」(de-communization)與德國「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的經驗,主張中國必須進行:
• 公開全部毛時代檔案
• 為大躍進、文革平反並國家賠償
• 廢除毛像、毛詩、毛語錄在公共領域的強制地位
• 將毛澤東從憲法序言與黨章中移除
• 設立「毛時代罪行調查委員會」(類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3. 毛澤東是中國20世紀最大災難的總設計師
——蘇曉康把毛時代的三大災難直接歸罪於毛本人:
• 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 → 毛的「超英趕美」狂想
• 文化大革命 → 毛發動並親自領導
• 黨國極權體制的定型 → 毛一手締造
——他認為若不把這三條「原罪」說清楚,中國人永遠無法面對自己的歷史。
4. 當下的習近平時代是「毛澤東復辟」
——蘇曉康在2013年就斷言:「習近平不是鄧小平的繼承人,而是毛澤東的隔代復辟者。」
他列出十大復辟現象:
• 唱紅打黑
• 個人崇拜復活(「習核心」)
• 廢除任期制
• 左派網站(如烏有之鄉)重新得勢
• 「英烈保護法」把毛澤東變成不可批評的神
• 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國慶化
• 毛家灣、韶山成為政治朝聖地
• 毛語錄重新進入教材
• 對文革的正面評價開始出現
• 對「非毛化」言論的全面打壓(高兟被捕就是最典型案例。
5. 「非毛化」是被鄧小平主動放棄的歷史機會
——蘇曉康認為1981年的《歷史決議》本來有機會徹底非毛化,但鄧小平為了保黨、保自己,採取「三七開」(功大於過),結果留下了「毛澤東思想」這顆毒瘤。
——他把這稱為「中國現代化的原罪」:用經濟改革代替政治改革,用「摸著石頭過河」代替歷史清算,結果導致今天「毛澤東的幽靈重新附體」。
6. 非毛化才是真正的「告別革命」
——他批評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論太軟弱,只反對暴力革命,卻不敢觸及毛澤東這個「革命的總根源」。蘇曉康說:「不告別毛澤東,就不可能真正告別革命。」
7. 非毛化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
——蘇曉康對台灣朋友說得很直白:「只要大陸還掛著毛澤東像,還把毛當建國之父,台灣人怎麼可能接受統一?統一的前提是先把毛澤東像從天安門摘下來。」
8. 非毛化是底線,不是選項
——他多次說:「非毛化不是我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中國要不要走向現代文明的問題。誰反對非毛化,誰就是中國現代化的敵人。」
9. 當下的沉默與遺忘,正是毛毒復發的溫床
——他最痛心的是年輕一代對毛時代的無知與麻木:「今天的大陸年輕人以為毛澤東只是個可愛的『毛爺爺』,這正是毛毒最深的表現。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是被這個『毛爺爺』害死的。」
10. 非毛化最終要靠中國人自己完成
——雖然流亡海外30多年,蘇曉康始終不相信「外力推動」。他說:「東歐去共產化是靠自己人,德國去納粹化也是靠德國人自己。中國的非毛化,最終要靠中國人自己覺醒。」
總結蘇曉康35年的立場:
他不是要「消滅」毛澤東,而是要「把毛澤東放回歷史該放的位置」——一個造成中國20世紀最大災難的極權領袖。
只要這一步不完成,中國就永遠在「毛澤東的影子」裡輪迴。
而高兟被捕、鐵流被判監、毛左網站復活、毛像重新被保護……一切都證明:
蘇曉康1989年說的話,今天變得更加真實——
「不非毛化,中國無寧日。」
附:光棍、枭雄、混世魔王——「非毛化」三家
“评毛”至今还是一种文化评论,没有进入学术层次。
“评毛”资源可分两种:西学的参照和中国史观的看法。
谈三个人的观点。
一、余英时
“评毛”仅偶一为之,但他是中国人文界当代第一人,所以看法珍贵且重要,余引中西两法说毛,有一句话最经典:“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1、传统秩序崩解下的“光棍”
余英时1993年10月23日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评论,至今没有评毛文字超过它。
余提出一种“边缘人”的观点,指出: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这个“下层社会”是指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即“社会边缘的人物”。中国历史反复演出的,就是王朝崩溃之后,主流社会解体,大量的能人流落在底层,啸聚山林,扛旗造反,刘邦、曹操、朱元璋都是这类人物。
余指出:毛泽东在党内逐步取得主宰,可视为“农村边缘人”战胜“城市边缘人”,因为中共早期领袖都是上等文化人;毛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2、“反常规化”的枭雄
余早就引入韦伯“奇理斯玛”式权力的论说来诠释毛。这种理论认为,魅力型权威一般需要经过一番“常规化”的转换,放弃“奇理斯玛”,才能换取长期稳定的统治。余指出,毛在这方面是居然是“史无前例”的,既不追随中国的汉高祖刘邦等,也不跟外国的希特勒、斯大林学习,因为后者最终都走向“常规化”而维持独裁,毛却是彻底地拒绝“常规化”直到死亡。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后,余又做了一篇大文《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依照韦伯理论再次一一列举毛的“反常规”:
——“谈笑风生榻上居”,毛27年统治与无数阳谋阴谋,都是躺在一张特制大床上想出来的,一个绝妙的“反常规”隐喻;
——不当国家主席,可以为所欲为,他跟一切常规礼仪都格格不入,宁愿“退居二线”,更方便搞阴谋;
——继续以“农村包围城市”,他反对“常规化”的办法,还是农村“打土豪”的阶级斗争那一套;
——信手操弄“群众运动”;
——反现代化的“否定意志”,毛对现代世界的惊人无知,如乌托邦空想等等。
再引一段余拿毛与曹操比较的文字。毛自己很认同曹操,然而汉末的曹操,虽然“不信天命”,但是仍然相信有周公这样的伟大人格,所以还不是一个肆无忌惮之人。毛虽然熟读历史,却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全都是权谋机诈的东西,所谓满眼看去都是“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在从能力上来比较,曹操是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毛只是一个乱世奸雄。
二、林毓生
余英时和林毓生,是治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两位大家,而在他们两位所建筑起来的基础上,这种研究至今没有什么进展。也可以说,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就避不开毛泽东,所以林毓生的评毛,也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
余林两位,都判定中国近现代是一个激进化思潮泛滥的时代,原因当然是中国儒家传统的衰微,又面对西学东渐,自晚清以来的几代中国士大夫,或者也叫知识分子,他们焦虑、性急、束手无策、饥不择食,率先领导一场否定自身传统、全盘接受外来价值系统的思想文化革命,到“五四”运动达到高潮,将中国推入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直到价值体系的无底线的一个崩解过程,至今没有停止。当然,这是一个比毛泽东大得多的课题,然而毛正是这个解体过程中出现的魔鬼。
林对近现代激进化的定义,比余更彻底,称之为“整体性的、全盘否定的反传统主义”;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思潮的根源,正好来自儒家思想模式“道德优先”的特征,也叫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靠儒家意识形态,来统合三块:上层官僚、中层乡绅、下层宗法家族,形成大一统社会;这种社会一旦解体,只有从道德上重新整合。
林是指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至上而且封闭、导致巨大灾难的第一人,他也进一步在这个思路下,分析了毛泽东以乌托邦思潮带给中国人的巨大灾难。
林毓生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描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比你较为神圣」的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的乌托邦主义性格”,这种「乌托邦性格」,颠覆传统与受制于传统,他分析了几个特点 :
——毛式乌托邦一反「乌托邦主义」不知如何在当下落实的基本性格,强悍地认定确知如何当下落实其崇高理想;
——它的现世宗教性(人的宗教)愈强(愈想把人间变成天堂),便愈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政治手段;而愈是不择手段,便愈需要从现世宗教性那里获得正当性,其结果是,从自认乃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变成一个无知、反知、无能、乱管的「 上帝」;
——「五四」真空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愈是摧毁传统才愈有可能进行彻底的建设,而中共的破坏愈彻底,便愈摧毁了知识分子不依赖强势意识形态(全盘化解决的导向及其答案)的能力,即﹕使得往相反方向多元思考的能力变得愈弱;
——最后,以全盘化反传统而取得极为强大正当性的中式马列主义,因其自我声称的一整套全盘化解决办法灾难性地落空,从而恰好完成了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逻辑的解体过程。
林的这个分析范式,可以对「大跃进」、「文革」、「改革」直到「六四」这一连串的灾难,获得一个逻辑的历史解释。 「大跃进」与「文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毛泽东以一个更大的灾难去补救前一个灾难的强悍行为;那么,邓小平的「改革」,何尝不是以另一种形式的灾难,去补救毛泽东的灾难?特别惊人的相似之处,是「改革」与「六四」的因果关系,正好是「 大跃进」与「文革」关系的重演,前后两次以错纠错的非常手段,在理直气壮、封闭和排斥任何不同意见的强悍性上,如出一辙。 不同之处只在于,邓小平的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没有毛泽东那种强烈的现世宗教性可以用来彼此加强,反而更加赤裸裸的残酷,说明这个封闭系统的解构本身,可能还是会以灾难形式发生。
三、康正果
康是我们同龄人,其著作《还原毛共》,继承前辈遗绪,且拓深并细化,在今日中文话语中,堪称空谷足音。
我认为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一章对青少年毛泽东自称“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分裂人格的诠释,颇系统地解构一个底层少年在末世挣扎,从小就具有的反社会草莽倾向,以及厌学、反智、理直气壮作恶等等性格成长的脉络。很少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
这本书的基本思路。清廷崩溃后,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最大难点,是建立宪政的途径,西方称为“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而中国则是皇帝之后是强人、强人之后是军阀、军阀之后是党棍,分崩离析,共识难成;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乘此天下大乱之际,先在边区夹缝地带,靠地痞搞“农运”、靠土匪搞“割据”;接着又在日军侵华、国军主力浴血抗日期间,躲在陕北发展壮大;最终借美国的幼稚调停、靠苏联的武器装备,以血腥内战,彻底断送这个“建制议程”,暴力夺取政权。
康也指出,毛泽东在党内的崛起,同样不择手段,从江西到延安,他是靠抗拒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控制,而取得党内主宰。所以康著的副标题是:“从寄生幸存,到诡变成精”。
最后,我想借刘晓波批毛的“六点”来结束,这出自于他的那篇著名的《混世魔王毛泽东》。
1、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2、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3、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4、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5、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6、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
四、一書:啟動一場「非毛化」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海外
細看(放大)這本書的封面,果然印著「助編——石文安 Anne F. Thurston」,這後面有一段故事,讓我知道在英文世界,文字版權煞是一樁大事。2017年夏天我們請 Anne 來波多馬克文化沙龍談這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蘭登書屋出版此書的署名很複雜,稱「本書原稿是中文,由底特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鴻超英譯、黎安友撰前言,Anne 為助理編輯」,但是在英文版封面上又突出作者李醫生和 Anne 兩人。
演講中 Anne 敘述了這段經歷頗為不快,我記得她用了一個詞 devastating ,非常傷心。據說李醫生最早將書稿送到普林斯頓大學卻未被接受,轉而再找哥倫比亞大學 Andrew Nation(黎安友)教授,於是黎成為這本書的靈魂,他招募 Anne 前去採訪,Anne 跟我說,她帶來一個助手,在芝加哥採訪李醫師,錄了幾十盤磁帶,再回來紀錄磁帶,颇費功夫,但那卻是李所不樂意的方式,想出書又無奈,便是這個結局。以我閱讀的感覺,這本書的思路和寫法,顯然出自西人而非中國人,而這本書的價值,恰是有一種非中國的價值觀,貫穿其中,那一定來自Anne,但故事是李醫生的。
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啟動了一場「非毛化」——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海外,因為它提供了「評毛」的最佳資料,而「評毛」在中國至今停止、曖昧,甚至已經出現毛的繼承者身居大位,整個世界對此毫無覺察——有點像當年希特勒上台,而歐洲很麻木。
《肉像與紙韻:康州筆記》2006
A Paper Ritual in Sound and Dance Conceived and created by Tan Dun and Muna Tseng無聲的震撼──與約翰.凱吉的最後談話
The Pink – A Performance excerpt
A Paper Ritual in Sound and Dance
Conceived and created by Tan Dun and Muna Tseng.
Choreography and Direction: Muna Tseng
Music and Sound: Tan Dun
A collaboration by Muna Tseng Dance Projects, New York; City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 Hong Kong; and La MaMA E.T.C., New York.
https://www.munatseng.org/works/PAR 表演藝術雜誌:::
 1992年6月12日凱吉和譚盾在凱吉的工作室。(Andrew Culver 攝)
1992年6月12日凱吉和譚盾在凱吉的工作室。(Andrew Culver 攝)里程碑 Milestone絕唱
無聲的震撼──與約翰.凱吉的最後談話
John Cage(1912.9.5〜1992.8.12)
美國當代最偉大也最富爭議性的作曲家約翰.凱吉,在今年八月十二日離開了這個充滿聲音的世界。他對音樂界最大的貢獻,是將「機遇」(chance )的觀念引入音樂創作,同時由於他對東方哲學宗教的嚮往和涉獵,他以易經六十四卦象的產生來解釋聲音與曲譜間的意義關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音樂美學影響了全世界:「聽而不聞則罔。聲音本來就是和諧的,包括人們所謂的『噪音』。所有我們的行動作為,都是音樂。」
文字|譚盾
攝影|Andrew Culver
試刊號 / 1992年10月號分享至facebook
John Cage(1912.9.5〜1992.8.12)
美國當代最偉大也最富爭議性的作曲家約翰.凱吉,在今年八月十二日離開了這個充滿聲音的世界。他對音樂界最大的貢獻,是將「機遇」(chance )的觀念引入音樂創作,同時由於他對東方哲學宗教的嚮往和涉獵,他以易經六十四卦象的產生來解釋聲音與曲譜間的意義關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音樂美學影響了全世界:「聽而不聞則罔。聲音本來就是和諧的,包括人們所謂的『噪音』。所有我們的行動作為,都是音樂。」
八月十二日的電話答錄機
晚上,我像往常一樣開始檢聽我的電話答錄機:
「譚,John去世了……」(馬修.卡畢,紐約畫家)
──哪個John?我急問自己。
「我剛發了一封信給他。可是聽人説John Cage去世了,是真的嗎?」 (高橋,日本鋼琴家)
──My God.
「他悄悄地走了,就像他平時在他音樂中寫下的那麼多的休止符一樣。不過,這次他寫下的卻是永遠的休止和寂靜。」(伯莉尼絲,法國影評家)
我儍了。像是被冰凍住了一樣。我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刻抓起了電話──接電話的果真不是他。羅娜(John的生活助理之一)説,「是真的」。我説我昨天下午和他還在電話上説笑,怎麼……「是的,像往常一樣,他忙了一天,直到下午六時左右,突然中風,倒在地板上後就再也没有起來……。」
John,你失約了
十一日下午三點多鐘,我打電話給凱吉,是因《藝文,異聞》電視節目託我問他能否接受訪問,談談最近世界各地爲他八十壽辰而舉行的一系列活動及介紹一下他的新近創作。電話剛通,他就馬上問我「炒蘑菇可以加豆豉嗎?」我説當然可以,並告訴他我媽媽吃甜點的時候還加辣椒醬呢。「瘋彺的湖南人!」他説。談笑了一陣子,他答應了訪問。我問他能否在八月底接受採訪,他説因二十七日他要去德國開音樂會,最好提前一些。我説只要他行,哪天都可以。所以我們約好八月二十日中午十二點鐘在他家裡見。最後他對我説:「譚,下週四見」,誰知道這卻是我們最後的道別。十三日早晨,我讀著紐約時報頭版刊登的約翰的遺像和他去世的消息,終於意識到他已經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下週四他也不會來見我們了。這次他失約了。
十三日的紐約時報
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十分罕見地,幾乎用整版的篇幅報導了這位本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在音樂、表演藝術和觀念藝術最有影響的「音樂革命的開拓者」約翰.凱吉的逝世,並極高地評述了這位大師對二十世紀文化藝術所作的傑出貢獻和他引人爭議的一生。
Throughout her creative career, she collaborated with other well-known artists such as Jasper Johns, Robert Rauschenberg, Larry Rivers, composer John Cage, and architect Mario Botta, as well as dozens of less-known artists and craftspersons.
凱吉不但是作曲家,也是作家和哲學家,他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音樂的領域。五十多年前他在美國西雅圖的康尼西藝術學院和後來成爲美國本世紀最偉大的編舞家之一的模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成爲同學後,便開始對康寧漢舞蹈學派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他鼓勵康寧漢在紐約成立了舞團,自己擔任音樂指導,並參與了幾乎所有康寧漢傳世之作的創作和演出。凱吉的創作觀念不但還影響了他的好友們如傑出的現代藝術家傑斯伯.强斯(Jers-per Johns)、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更啓發了好幾代的表演藝術家和歐美及亞洲的年輕作曲家。約翰.凱吉一九一二年九月五日生於洛杉磯,曾隨「十二音無調性音樂」的鼻祖荀伯格(Arnold Schoen-berg)做學生,但荀伯格從不認爲凱吉是個作曲家,而稱他爲「天才的發明家」(凱吉自己常引此爲榮)。年輕的凱吉當時很窮,没錢繳學費,但荀伯格還是免費收了他,只要凱吉發誓終生奉獻音樂。凱吉答應了,並一生勤奮、多產,直到他去世前幾分鐘還在寫作,他的書桌上仍遺留著爲奧地利國家廣播電台没有寫完的管絃樂手稿《58》。
無聲的震撼
凱吉在三十年代末開始實驗在鋼琴中置入螺絲釘、木頭、金屬片、紙張等物,使之發出既令人驚訝又覺得熟悉的聲音,終於把傳統的西方音樂文化審美拓寬到更加豐富多元的世界裡,爲後來西方音樂意識和非西方文化意識間的相互理解、溝通開啓了一條嶄新的路。他三十至四十年代爲裝置鋼琴(Prepared Piano,或準預衆綱琴-編按)而作的一些作品早已使他成爲西方古典音樂中前衛派的領導者。四十年代到了紐約後,凱吉開始對東方音樂、《易經》及禪學產生極大興趣;特別是對中國《易經》的興趣和研究,終得使他開始了對各種自然之聲如水、沙、螺殼、風及收音機、生活用具、留聲機、工廠垃圾、街道交通樂音和磁帶剪接音樂等音響和音響材料的創作實踐。他是本世紀的第一個革命者,開始改變和打破了在歐洲文化史上延續了六、七個世紀的音樂語言和音樂結構,並把人們對音樂的審美從宮廷、教堂和舞台帶回到大自然。他曾説世上從來就没有噪音,而只有聲音,「我還從來没有聽到過我認爲永遠不願意再聽一次的聲音」。由此可見,他已把音樂創作的材料使用觀念提高到了一個無限的境界。除了對聲音的實驗,他認爲寂靜(silence)也是一種聲音。他於一九五二年創作的〈4’33〞〉,即四分三十三秒的寂靜被分爲三個樂章演奏,這首無聲的音樂作品當時震撼了全世界。然而,今天他的確是已經悄悄地離開了這曾被他震撼過的世界。他已經習慣寂靜了。他這次突然地、永遠的沈默再一次震撼了世界。
「資產階級現代派的極端頹廢代表」?
其實,一九七九年我在北京就聽説過這首〈4’33〞〉和凱吉的名字,不過那時北京的雜誌、報刊和某些極左「音樂家」常把這首曲子和凱吉作爲一個「資產階級現代派的極端頹廢代表」稱之。但願北京現在没人再這樣批評此人此作了。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十年後,我在紐約市威特利博物館第一次聽到了鋼琴家瑪格萊特.陳靈演奏〈4’33〞〉,那天凱吉本人也在場。演出之前他曾向觀衆説「其實絕對的寂靜你是永遠聽不到的,我能做的只是想在這四分三十三秒内讓你能真正集中精力在所謂的寂靜裡聽到你自己,聽到在我們生存的環境裡一切可能偶然發生的,但也非常習慣了的聲音。這些聲音每時每刻都有美妙得不可數的變化和它們自然的組體(texture)與對位(counterpoint)。同時,我也認爲寂靜是聲音的一種。」我聽完這首作品後很感動,也很感激凱吉讓我聽到了那些我天天置身於其中卻又從未聽到過的聲音。那天音樂會後我想了很多,從「大音希聲」到《樂記》,從「此處無聲勝有聲」到「音樂必須爲社會主義服務」,我還想到這大概是世上唯一的一部每次演出都不一樣,且永遠不會重複的作品──在每一次的寂靜裡,你能聽到的聲音都是不一樣的。當時我聽這位「現代派的極端頹廢代表」的作品時的心境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聽老師講老莊和嵇康的音樂美學時的心境是一樣的。
烹飪與作曲
我第一次聽凱吉的音樂會是一九八六年我剛從北京到紐約那會兒,記得有次在紐約下城的音樂會上,他穿著一套灰色勞動布裝(後來發現無論任何場合,他永遠穿著這套衣服)在台上解釋他的作品,聲音低沈並有些沙啞,但極爲平和。那天他談了很多作曲與烹飪的話題。對此我感觸很深,我的確也認爲寫音樂就像炒菜一樣,把什麼樣的菜、色、味調在一起,火候如何,放多少鹽,要不要放醬油等等就如同作曲的結構、配器和音樂想像一樣。不好的廚師,有最好的菜、料也不一定能做出好菜來,而好的廚師卻能在那道菜還没有被炒出來之前,就已經看到了它並嚐到了它。一個好的作曲家一定要有好的内心聽覺,在他往往還没有把腦子裡的音符一個個寫下來之前,他定已聽到了他想像的聲音甚至整個作品了。我想繪畫和編舞的過程大概也一樣吧(也許我錯了)。記得有次我和凱吉開玩笑説,荀伯格收你做學生之前,先要求你發誓定把終生奉獻音樂,下次有人要向你學作曲的話,你得先讓他做頓飯嚐嚐,看他炒菜的想像力如何而決定是否收留他。
第一次和凱吉深談
正如紐約財報首席音樂評論家愛倫.柯森(Allen Kozinn)所説,凱吉是一個和氣的人,他總是喜歡和年輕人交朋友。他常常出席紐約下城的很多音樂會和藝術活動,而後總是微笑地、從不倉促地和觀衆們、朋友們交談很久,有時直到劇場管理人員催離幾次後才回家。就這樣,我經常有機會見到他,和他聊天,他也來聽過我的音樂會並親自爲我交響樂專輯的出版寫了前言。而我真正和他長時間交談,卻是他去世前兩個月的那天,六月十二日我們約定在他家裏談一些工作上的問題。當時因我受日本Suntory音樂廳及該廳音樂總監武滿徹先生委約要和東京交響樂開一場音樂會;按規定,這場音樂會除了演出被委約的作品外,還必須由被委約的作曲家選出兩位他認爲對他一生創作影響最大的作曲家,和一位必須比他本人更年輕的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一同演出,有點「過去、現在、未來」的主題意味。對我最有影響的作曲家,我選了有蕭斯塔柯維奇和約翰.凱吉,由於要討論選指揮、獨奏家、分譜、錄音、日程等問題,我們幾乎談了三小時之久,除了談工作,我們也談了些其它:
譚盾:一九八八年在中美藝術交流中心周文中教授召開的台灣、大陸中國作曲家交流的酒會上,前中國文聯主席吳祖强和現台灣國立藝術學院院長馬水龍均邀請過您去台灣和大陸訪問、講學;但那時您説走不開,等過兩年再説。您現在仍想去中國走走嗎?
凱吉:一直想。我去過遠東多次,但就是没有去過中國大陸。你知道我非常喜歡老子和莊子,《易經》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很想去易經的故鄉看看,作爲一個學生去。但現在仍有幾種作品在完成中,還是走不開。我想九十歲以前一定要去。(接著他大笑了很久,他常這樣。)説正經的吧,後年去。
譚盾:你常提到蘑菇對你的生活和創作也有很大影響,那是爲什麼?
凱吉:我年輕的時候在加州,很窮,常靠採蘑菇吃過活。後來,剛搬到紐約時,住在哈德遜河邊,那兒也長滿了蘑菇,我後來學會了辨別它們,它們對人的身體和思維都有好處(説到這裏,他給我看了一些他在世界各地採集的蘑菇,我們聞了好一陣子,它們散發著一種特殊而又質樸的芳香)。我和蘑菇的關係,正是我和自然交往的一方面。人要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份(當時我們在吃中飯,桌上近處是一些黑麥麵包,中間是中東的豆粥,遠處是中國的辣椒醬)。我們從西方開始(他遞給我一些黑麵包),接著你可嚐些「中東」也可吃點「遠東」(大笑)。
譚盾:荀伯格曾是您的主要老師,但你們的音樂完全不一樣。難道您從來没有受過一點兒他的影響嗎?
凱吉:没有。我一直不認爲可以把聲音分成一格一格的(指各種音階、音列)。我認識聲音是把它們看作一塊整體,一塊從高到低從小到大的整體。世界上有這麼多聲音,爲什麽作曲家只能用那幾格音呢。
譚盾:中國京劇的韻白、行腔就是在那個「聲音整體」裡完全自由地游走,而不是在某部音階上的跳動。
凱吉:我很喜歡京劇。我這個人從來就没有和聲的感覺。我没有讀過荀伯格的和聲學書。其實荀伯格最後還是對我説了這樣的話:「和聲是没有規則的。」荀伯格是一個偉大的人,光從他的這句話裏,我就學到了很多。
譚盾:您這一説,我的確覺得很難想像。畫家只用叫得出名的顔色作畫,但是,我也在你的作品裡聽到了「無調性音列」。
凱吉:是的,這些所謂的樂音,也在我的「聲音大家庭」中。但我告訴你,當初一位舞蹈家要我爲她的一部非洲風格的作品作曲時,我曾試了很久,想用某種「十二音列」造出那個「非洲」來,結果我一直失敗,後來我開始在鋼琴内部作裝置實驗,我找到了。那位舞蹈編導也很滿意。這就是我爲什麼要「破壞鋼琴」的原因。
譚盾:九月五日是您的八十大壽。現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爲此舉行您的音樂會。您這麽大年紀了,仍天天寫作嗎?
凱吉:是的,去年我寫了幾部管絃樂作品。昨天我剛剛拍完一部電影,它是我最近這個作品中的一部份,演出由管弦樂團、光和電影組成。夏天會在德國演出。
譚盾:您時間夠用嗎?
凱吉:不夠。我每天早上七時起床,印地安人説最好日出的時候就起來。快八十歲了,你突然發現以往的你的那個身體開始向你提出很多需要實驗的問題,我甚至發現每天早上從床上坐起來都越來越困難了。我天天試著如何更容易從床上坐起來。寫字和寫音符對我來説也越來越困難了。
譚盾:那您仍有寫大作品的計劃嗎?
凱吉:當然。我現在在和模斯.康寧漢一起構思一個大作品,叫《海洋》(Ocean)。這是一個環型的表演作品,舞蹈在中間、音樂家在舞蹈的外圍組成一個環,奏出海底、海上和陸地的聲音,觀衆在上方俯瞰整個演出,還有光、電影、動物們的參與。
星期五晚上的音樂會
可惜,凱吉的很多作品都還没有寫完,大自然就匆忙地把他召回去了。
像前幾個週末一樣,凱吉去世後的第一個星期五的晚上,紐約現代博物館的雕塑公園内擠滿了他的觀衆,但那天晚上人更多,更寂靜,唯獨凱吉自己没有來,那晚是凱吉的〈Europera 5〉在紐約的首演。整個作品的演出由燈光系列變化、環型流動的立體聲音效,老式手搖式唱機、收音機、八部電視機、鋼琴及二位女高音擔任。
手搖式唱機在粗糙的唱針下呻吟著十九世紀的咏歎調──鋼琴家在樹下獨自聽著自己的演奏──光的運動不停地把我們從白天帶到黑夜,從地球帶到半空──寂靜──電視機無聲地顯示著電視台正在播放的肥皂劇──街上不斷傳來交通的吵雜聲──歌唱家們不停地改變著方向在歌唱(像是在練聲)──又是寂靜──環型的立體聲喇叭裏不斷沖出剪接過的歌劇大全奏的巨浪,此起彼伏,好像你就坐在柯波拉(Francis Coppola)身旁觀看《現代啟示錄》的現場拍攝一樣,華格納歌聲中武裝直升機在田野上捕食著人羣;沖浪;天空下起了巨大的「血」,人們的叫喊──寂靜──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那台手搖唱機仍在唱著粗糙的歌……幾秒鐘後,唱機手搖發條再也無力了,那唯一的歌也中斷了。
──寂靜──
在作品的最後,觀衆爲凱吉加寫了近二分鐘的休止符。人潮中,我擁抱著安德烈. 卡文(凱吉的藝術助理),是他指揮了今晚本應由凱吉本人指揮的首演。他對我説:「謝謝你來看演出。」我説:「你還好嗎?」他答道:「我不相信約翰已經走了。我仍天天去他工作室上班。」安德烈説話時總是微笑著,此時也一樣。但我看到了他的心在流淚。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六日於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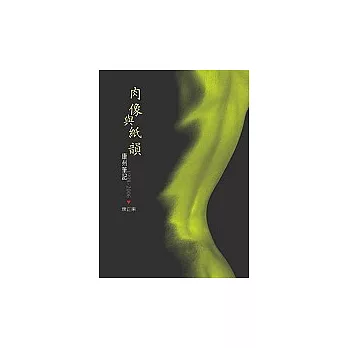
肉像與紙韻:康州筆記
作者: 康正果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06/10/01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常見字詞
------
譯作
岡布里奇著:《藝術的故事》(與黨晟合譯),陝西美術出版社,1987。
安妮·厄努著《只是戀情》,香港明窗出版社,1996。
康正果《肉像與紙韻》,台北允晨文化,2006。
康正果《泛文與泛情》〈詞淫和意淫〉意淫空間 ,台北:允晨文化,2024
明人王次回及其《疑雨集》.....鄭清茂校的版本(台北聯經),翻過幾次, 都不及康正果的〈詞淫和意淫〉(參見《泛文與泛情》2024)中說的"覓妾"史,該書發楊台大教授提出的"意淫空間 "....
內容簡介
現在白天做"像公事點"的工作,晚上自由閱讀。今天讀康正果老師的【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台北:允晨文化,2005)。難免為歷史興嘆:本書末頭,下一代回上海打拼,康老師或以為,美國籍是"黨天下"下的護身符,......這可能也很難說。
Kang-i Sun Chang
My colleague Kang Zhaneguo 康正果 and his wife Fang Xiuqin’s 方秀芹 poetic response to YU Ying-Shih 余英时 and Monica Yu’s 陈淑平 new years’s greetings!
得英時、淑平特製“戊戌春回”新年賀卡,細玩詞義,賦詩回應。
風雨淒淒議改良
莠民野火焚昆岡
百年殘暴易殘暴
梗阻維新興舊邦
世界潮流浩浩長
擋車螳臂徒猖狂
慶豐包子兜著走
夢醒黃粱必斷腸
英時、淑平
新年快樂
正果、秀芹敬賀
2018年2月13日
康正果,1944年7月2日出生於陝西省西安,祖籍陝西臨潼,美籍華人[1],現居於美國康乃狄克州北港,中文教師、作家、文史研究者。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曾執教西安交通大學,美國耶魯大學[2]。評論隨筆散見大陸、港台和北美報刊。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公共知識分子。
簡歷
[編輯]- 康父在文革中幽憤而亡,康正果曾於1964年被陝西師大作為反動學生開除學籍,繼而以「妄圖與敵掛鉤」罪名勞教三年,釋放後長期在西安附近農村居住。
- 1979年平反後返回陝西師大讀書。
- 1982年 陝西師範大學碩士畢業後在西安廣播電視大學任教。
- 1984—1994年 在西安交通大學任教。
- 1994—2012年 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
- 2012年7月以senior lector emeritus從美國耶魯大學退休在家,現為自由撰稿人。[3]
著作和譯作
[編輯]- 岡布里奇著:《藝術的故事》(與黨晟合譯),陝西美術出版社,1987。
- 《風騷與艷情》,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1年台北雲龍出版社繁體再版;201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修訂版。
- Aimee E. Liu著《愛·謊言·陷阱》(與蕭瑗合譯),台北旺文出版社,1993。
- 《女權主義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安妮·厄努著《只是戀情》,香港明窗出版社,1996。
- 《重審風月鑒》,1996年台北麥田出版社繁體版,1999年遼寧教育出版社簡體版。
- 《交織的邊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 《鹿夢》,台北三民出版社,1999。
- 《身體和情慾》,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 《生命的嫁接》,上海三聯書店,2002。
- 《我的反動自述》,2004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初版,2005年台北允晨文化更名《出中國記》再版。2007年英譯本Confessions:Norton Press版;2011年義大利文譯本出版。
- 《肉像與紙韻》,台北允晨文化,2006。
- 《平庸的惡》,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
- 《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 《還原毛共》,允晨文化,臺灣,2015。
家庭
[編輯]參考資料
[編輯]- ^ http://www.epochtimes.com/gb/1/5/2/n83847.ht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康正果:惡夢還在惡
- ^ 康正果. [2012-1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09).
- ^ Surviving Under Mao: A Slacker’s Guide. [2012-1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17).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