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芬伶(1955年-)教授的14歲,約1968~69。(昨天老曹看到《周芬伶精選集》 ,談起某次回母校評審小說獎的故事。......)
她說:"十四歲到東海旅行,當時覺得好荒涼,沒想到會在這裏停留這麼久,教堂的玻璃窗似乎有神之光輝。"
我可能在1967~68 初次到東海。印象最深的,不是教堂,而是一位可能是生物系的男生,在校長室下方,邊走邊走向文理大道......究竟講些什,我忘了。也許在初高中碰到的大學"畢業生",都沒那樣年輕.....
(據說,取名"東海大學",董事會覺得可以,就用了,沒人去查日本已有同名的大學。也沒人像梁容若教授退休到"靜宜文理"教書,可以寫出"閒話靜宜".......)
等了好多年,包子不一樣了…….
離第一本書《敲昏黥魚》寫序相隔十三年,他停筆約八年,而我已七年未見他。二零一七年我的小說發表會上,他站在最後方,會後我坐在椅子上跟他說話,他半蹲在腳邊像孩子般說不想再寫,再問一次,他一直搖頭,回家後寫信給他,看到你一直搖頭,心都碎了。他回信說了一些理由,但不一定是真正的理由。
有些人連呼吸都感到痛苦,隨時感到傷害在發生,寫字只是暫時固定自己的方法之一,出書帶來的自我懷疑更多,當他說不寫時,一定是真實感受到書寫帶來的痛苦無法承受,這時只能任他去。這七年來我沒再問他,我知道就算沒有寫作,他也能過得自在。如他當年所說,他的願望是在民宿打工,一個月一些生活費就夠了,打掃完房間,看書寫字…這就是他心目中美好的生活,我知道他不會離開台中,可能正打著工呢,每天回去陪陪母親;或許在某一天,他會拐進小巷某間咖啡屋,每個城市都是他的民宿,每個咖啡屋都是他的書房,他會點一杯咖啡打開電腦,敲出一些絕妙的文字,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他會寫出驚人的東西。不管他一再搖頭,我相信會有那天。
有些寫作者或為寫作躲起來,或為不再寫作消失,或者寫一輩子從不發表,那是他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許多好作品都是這樣產生的。
七年後,我們相約見面,聽說寫了一個長篇,這些年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跟期待讀他的小說一樣好奇,我要聽他自己說,不多問只聽著。見面之前,他先寄來寫好的二十六萬字長篇,初讀覺得是成熟的作品,跟之前型制較短相比,情節如行雲流水般自然,氣韻深長,主題沈重,寫法有輕有重。讀前一半覺得太正常,讀到後一半讓人屏息,這又太不正常,就四十歲小說家第一個長篇來說,跳好幾個等級,它給我們完全不一樣的包子。
故事大多集中在一個火山附近旅店裏,男主角杜有恆是打工仔,很會鋪床單,吸地板——有時小說比散文誠實,這裏面大概都在回答他這幾年的生活,他可能去作了田野,看了許多人,中年男子的散淡與沈緬於回憶寫得最多也最好,這裏面有折射也有作者的影子。\
死亡與自殺權及對存在的提問,這是小說常見的主題,值得一再叩問,只是如何寫出新意?
前面沒有動物,只有人物,這讓我覺得,嗯,他變大人了,不再玩動物了。一對母女來到火山
口,探索跳火山自殺的父親(祖父)生前的事跡,寫實手法,本土題材,嗯,變大人了。前半大約只用三分力,慢慢鋪陳,後面才用盡全力,讓你蹴不及防滑進時空的縫隙,人物、心理、動作、情緒描得越來越細,你不知道會後面會寫出什麼,只有一個又一個會流動的畫面。然後細節湧現,以放大的倍數具體浮出,那是一個斷裂且傾斜的時刻,世界如此被改寫。
從放大鏡鏡頭,到顯微鏡肉眼不可及處,細到無法切分,原來大魔王在後面,動物出現了,不是寫實,也不是量子疊加,或情景交融,而是撲向自己,所有的問題都拋回讀者身上。
自從存在主義小說提出人生無意義或不值得一活,卡繆以「團結」對抗死亡,米蘭昆德拉卻把死亡寫得輕如鴻毛,不管是輕盈的托馬斯或沈重的特瑞莎同時希哩糊塗地被撞死於車禍中,
這是死神的公平——當死亡無可逃於天地,我們握有死亡權或自殺權嗎?人類對寵物執行安樂死,卻不敢面對安樂死的立法問題。一些宗教都主張人無死亡權,自殺必然永不超生,然死亡
一直來一直來,這是人權的厄夢,也是兩難。
想死的欲望跟求生的力量一樣強大,當小說主角決定跳火山那刻心裏想的是什麼,作者透過
追溯死者自殺前的生活,回到最後那一刻,像偵探般抽絲剝繭,一個個生動的底層人物出現,
小 P、保全、世紀末酒吧中的人、黑傑克……,包子用靈魂雕刻這些人,他們是主觀的也是客
觀的,寫時入神,書寫者潛入人物的心靈,形成一個又一個靈魂畫像,讓我想到果戈里的《死
靈魂》,那個買賣死者人頭戶的邪惡主角,讓亡者在主人或親友們的口述中復活,再活一次悲慘
人生,死者與生者同在——包子寫的也是生者在死者中,死者在生者中,生死並非兩茫茫,而
是清楚不過;然而人總是逃避,不能真正面對。所謂自殺之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會
有被死神襲擊的那一刻。
而自殺基因是否會代代相傳,無法想像才九歲的小福爾摩斯,要不了多少年,也將步上火山
旅程,聽說阿蘇火山是日本人自殺的聖地,上面佈滿崗哨,仍阻檔不住堅決求死的人們,也聽
說千萬不要靠近火山口,它彷彿有股吸力,令人想往壯麗的熔岩中走去;而北歐的冰河兩旁佈
滿鐵絲網,想死的人太勇猛,把鐵絲網都衝破,死亡的驅力如此可怕,讓我們不敢面對。
等七年才完成的小說,包子的變得氣更長,且更沈得住氣,不製造刻意的衝突,像冰山雪溶
般讓真相浮現,人物與動物寫得極神,我都可以看見黑傑克修理皮件的程序,聞到皮革的味
道,也能看到杜有恆、羅建東整理床單、用吸塵器吸到指甲片時專心致志的神情,他變得有耐
心寫一個史詩級的厭世小說,開頭很易讀,後面像當頭棒喝般將你打醒。不,厭世只是表面,
能直面死亡的人,常是最懂愛的人,愛戀生命與他人,如無他人,如何照見自身。小說是他人
的藝術,透過無數的他人,凝視且化入他們,即是去除一切界限的愛,也折射作者的哲思,同
情地理解與交感,才是小說精神的裏層︰
慟、驚恐、失落、懊悔、憎惡等等情緒的擊打。在這些情緒中唯有一種情續十分地輕柔、卻也令她最難以忍受,那就是理解,對父親的理解。是她不得不如是想︰父親和我一樣吧,我們身上都有那道隱密而特殊的印記。
他是否是以小說修行的覺者?或者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志的顏回?有時我這樣想,但也不確定,包子可能也不想被確定。問他讀哪些小說產生的靈感,他說是保羅奧斯曼《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那個善寫紐約,把這大都會寫成小社區,寫那些無奇不有的愚人愚行,他們大多是魯蛇不具備解救他人的能力,卻意外救贖自己與他人,包子說:
本書創造一個心靈受傷者的容身之所,作者溫柔地書寫這些柔弱之人,這些特點他原已有之,只是他這次更勇敢直接地進入悲傷的核心,那也像是火山口,岩漿發出赤紅的強光,連金屬岩石都溶化灰飛煙滅,也只有接近那個瀕死之點,才會放下一切執念與偏見,自我的消融,才是生命的出現;而這個消融的過程即是小說本身。
包子雖是七年級,更像五年級作家,是袁哲生、黃國峻、賴香吟的混合再造者,然他的柔軟慈心是他獨有的,在這個倒黑以為白的亂世,他的小說安靜且純淨,是濁世中的清音,亦是警鐘,他展開的心靈探索旅程,有一些是你想得到的,有一些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他以細密畫家的耐心畫出不可思議的生與死的交會縫隙,那裏彷佛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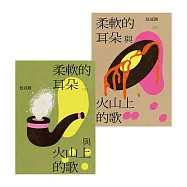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